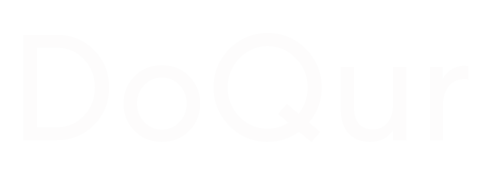首天電影票房九萬,這類國產電影不想總在夾縫中生存
《日光之下》的故事情節,出現在1999年寒冬的邊境地區小鎮,電影借谷溪、谷亮、天正、冬子四人的感情糾葛,牽扯出一段關於水域鬥爭的凶殺犯罪行為。
當時,有一名同鄉從家鄉安多來找德格才讓,表達了想出單曲的心願,花光了頭上的5000元。“他就是堅讚的原型,20年過去了,他現在開了一間扎念琴加工廠,仍在從事與音樂創作有關的事。”
“今天,中國的影片市場依然亟需具備地方、地緣民族特色的影片,不論是出自於青年編劇還是成熟編劇之手,這類影片仍須要被更多觀眾們看到。”
✎作者 | 蔣苡芯
2018年,為的是攝製《日光之下》,梁鳴大半日子在伊春度過。他見了更多帶有故鄉臭味的人,重新發掘他們自幼的記憶和物品,獨自一人走在小城的湖邊看短暫的春天一晃而過。“證實他們每晚無時無刻不與故鄉在一同。”
做為蒙古族第一位影片錄音師、第三屆“青蔥計劃”五強編劇之一,德格才讓攝製續集《他与罗耶戴尔》是想表達一件事——以不一樣的音樂創作表現形式為入口,呈現出當下內蒙古海南蒙古族自治州的新風貌。
用影片方式記錄“當下正在出現的變化”,也是為數眾多青年編劇正在順利完成的命題。
張大磊說,在漫長的籌備過程中,無法放置的“鄉愁”有時候也會毀滅他,看著文檔上人物的臺詞,或是腦海中時不時想到的一個片段,他會泣不成聲。直至看到影片在熒幕上放映的一剎那,張大磊才覺得,他們越過了鄉愁的一道坎。
原創 蔣苡芯 新週刊
去年11月27日,在平遙國際影展、澳門國際影展、香港國際影片節等均斬獲大獎的影片《日光之下》在全省藝術院線公映,截至今日截稿,總電影票房64.3多萬元,公映首天排片率僅0.3%,電影票房嚴重不足10多萬元。
但是,青年編劇也須要提防行業和資本的裹挾,不應盲目攝製過分陽春白雪的片子,只為在各大影展得獎賺錢,卻不在乎市場的接受和喜好程度。
梁鳴說:“你從中體驗到宿命世間的同時,也能體會到自己生命力的頑強。我想,全世界每片農地都理事長出屬於那片農地的獨有故事情節。當地人的樂觀、喜樂,或許我們未曾經歷,但是可以或理解或尊重或體會吧。”
《日光之下》困局背後,表演藝術影片或文藝影片到底該怎樣破題?在青年編劇的影片敘事中,又承載著多少濃郁的集體感情和個人思索?
《春江水暖》編劇顧曉剛,將中國山水卷軸的感人氣韻嫁接進影片。
棚戶區改建讓過去的平房被拆毀,衛星城蓋起的樓房沒有不同之處,長得都一樣,街道也有了信號燈。“越看會越懷念他們自幼的狀態和屬於小鎮的韻味。”
梁鳴回憶,在無數次的修正中,兩個人物的宿命走向始終沒有變化。故事情節不斷添加和修正的部份,還是關於身分疑惑、遭受、職業的變化。“可能將一開始也不確認他們究竟想要什么,只好造成了一個很長時間的試錯期。但那時仍未真正去想,家鄉究竟要在整部影片中飾演什么樣的配角。”
現如今,快手、抖音等短視頻運用已在內蒙古海南藏族自治州極為活耀。“我們那兒只不過沒有大家想像中閉塞,只是唱唱山歌、騎騎馬,現在內蒙古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孩子很風尚的,整個教區基本都曉得《中国新说唱》《热血街舞》那些電視節目。”
原副標題——每片農地都理事長出他們的故事情節
鄉愁在張大磊初中離家趕赴白俄羅斯唸書時,顯得愈發強烈。絕非即使離家千里才迸發,相反,他覺得,長達6年在異鄉獨自一人生存,他們找出了一個空間,“那個空間就是鄉愁所在地,它並非一個具體的物理學空間,而是你用五官去體會、沉浸的情緒,是屬於過去的、我跨不過去的一段經歷和時間,我要弄清楚”。
家鄉正成為青年編劇集體敘事的進口,自己在其中實現對自我的重新理解,也順利完成了自我表達。
梁鳴意識到“故鄉是他們的創作母題”這件事,是分階段的。如果說那個母題曾一度被遮擋,那么隨著其成名作《日光之下》從劇本創作、籌備攝製到得獎、公映的大力推進,這塊籠罩著他36年的大布,也一點點被揭開。
除此之外,梁鳴所觸碰的最大變化,還是人。他發現,愈來愈多的青年人與家鄉的關係不再。自己當中,近的去了哈爾濱,遠的到了瀋陽、長春、青島、煙臺甚至北上廣。“這些因人之間擁有密切感情帶來的喜悅,今天可能會缺失尤其多,換句話說完全消失了。”
2019年,《日光之下》在各大影展大放異彩,並被拿去與更多國外觀眾們對話時,梁鳴才發現,他們的影片有一種特殊性,而這是獨有的地理空間所賦予的,兼有傷感和唯美。
《八月》曾在2016年獲第53屆金曲獎最佳喜劇片獎,2017年又助張大磊贏得第8屆中國電影編劇聯合會本年度青年編劇獎。在去年的第4屆平遙國際電影展上,張大磊的續集《蓝色列车》首映禮,一票難求。
影片《八月》,編劇張大磊和攝影師呂松野都覺得,黑白更適宜這個非常簡單的二十世紀,但是能在寫實的同時,減少許多魔幻的美感。/豆瓣
“當時,我內心深處有很強烈的慾望,想表達對那些感情的無法忘卻。” 2012年夏天,梁鳴著手寫《日光之下》電影劇本。電影劇本磨了6年,易稿數次,他每年都用年份和月初來命名,有時候修正得多了,還發生了“春分版”“寒露版”“冬至版”。2014年,電影劇本又因梁鳴韌帶脫落須要養傷,被擱置了兩年多。
有幾天,梁鳴和攝影師駕車沿著營口、黑龍江、通化、延邊一路走,去尋找帶有西北獨有記號性的個案溝通交流。
羅耶戴爾,蒙古語,即文藝女神“妙音仙女”。/豆瓣《他与罗耶戴尔》海報
三部影片的大背景均為90二十世紀。對於1982年出生在青海的張大磊而言,90二十世紀是對他最為關鍵的二十世紀。張大磊記得,在他的少年時期,會時常接觸到蘇俄的音樂創作和影片,身旁的姐姐或大姐也常穿著愛爾蘭裙、戴貝雷帽,“儘管不知道為什麼他們所處環境如此,但由於自身的敏感,那些傷痕就存留在心靈裡,許多年後都難以忘卻”。
從白俄羅斯學影片歸來,張大磊想拍一部屬於自己回憶和情緒的影片。2006年歸國後,他就開始構築《八月》的電影劇本,2012年電影劇本正式順利完成,但因資金短缺等問題,直至2015年才殺青。
與梁鳴的後知後覺相同,對於“根”的找尋和上溯,始終長在張大磊頭上。
一次,他獲知有位老者90二十世紀返鄉後從事捕魚工作。忽然之間,那個人失蹤了,父母百般找尋都無果,以為他已罹難。兩年後,他回去了,經查問獲知,由於他捕魚時不小心跨過了國境線,被白俄羅斯邊防部隊抓了起來,卻沒有向其父母及國內邊境地區機構通報任何信息。
張大磊說:“我的計劃並並非要一兩年拍兩部影片,而是尤其渴求能再返回這個空間裡,換句話說與空間裡的人繼續生活。這不但是用影片交待他們的人生軌跡,也是對自己的交待。”
魏軍指出,現在的觀眾們很聰明,自己已不太討厭過分技術、討巧的東西,反倒更欣賞紮實講故事的電影,在這一方面,青年編劇有著樸質的競爭優勢。
特別是1994年,下崗潮帶來的生活形式變化、優質影片和爵士音樂的集中爆發、小升初帶來的社會關係發生改變、雙親工作變動,等等,都讓剛上小學的張大磊顯得內向、敏感,“想上溯鄉愁的來源”。
去年11月27日,在平遙國際電影展、澳門國際影展、香港國際電影節均斬獲大獎,獲得為數眾多關注的《日光之下》公映。梁鳴將那個故事情節放到1999年寒冬的邊境地區小鎮來講訴,借谷溪、谷亮、天正、冬子四人的感情糾葛,牽扯出一段關於水域鬥爭的凶殺犯罪行為,其中牽涉天然氣外洩債務危機、邊境地區武裝衝突、漁民身分尊重等時代議題,和上世紀90二十世紀末混改帶來的集體傷感。
如梁鳴所言:“影片也許沒有辦法順利完成對每一心靈樣品的觀察,但人如果能夠真實對應他們的生活狀態,或是能與他們的各式各樣感知並存,坦率真誠地面對他們的心靈,唯美的美感,不論是在影片還是在生活中,總會發生的。”
大學畢業於演出專業的梁鳴,做編劇前一直在做女演員,參演過婁燁的《春风沉醉的夜晚》《花》等經典作品。2012年秋天,梁鳴回家吉林伊春元宵節,故鄉的變化已不容忽視。
《他与罗耶戴尔》是一部音樂創作高速公路電影,在影片中,年長牧羊人堅贊自小愛好傳統扎念琴自彈自唱,想成為一位家喻戶曉的自彈自唱女歌手。但這時,現代人已開始使用新式打擊樂器曼陀林伴奏,且需出單曲就可以贏得我們普遍認可。只好,堅贊趕赴蘭州,爭取出單曲,同時實現對音樂創作結合的理解。
今天的影片市場給了許多人青年人予機會去表達,也許也須要,給與更多的故事情節予空間和進口。打破閉環,就可以讓好的故事情節和講故事情節的人流淌起來。
梁鳴說,絕大部分製作者都會有一個自然流動的去向。“我創作的開始就是流到了家鄉,家鄉又流入了我,我們形成一個循環。我覺得與家鄉緊密連接的人,或許更能發現許多人間的精采,寬容相同地域所發生的特徵和故事情節。”
今天,關於《日光之下》的電影票房深入探討在網上傳播,梁鳴發朋友圈則表示,在這種層面講,他的經歷是能夠引導其它懷揣夢想的年長電影人,即使他們是非編劇或現代文學專業出身,這種層面等於野路子,但“我一直在堅持,沒有放棄,能讓我們看見希望……”
讓“變化”獲得記錄
“或許像我們這種的影片人,做此類影片最初的初衷並並非為的是電影票房。但仍然希望有更多的觀眾們看見,能在熒幕內外鏈接彼此間的心靈,能與那個世界對話。”
從平遙回去後沒多久,張大磊和好友溝通交流:“鄉愁與懷舊有何差別?”這三個詞寫成英語是一樣的,但他覺得,鄉愁是與生俱來的,是一個人經歷、其本質和功能的代表;而懷舊可能將更偏向於一個有目的性的行為。
影片的主色,
在愈來愈多青年編劇日漸通過影片實現個人與農地感情表達的當下,中國青年編劇聯合會編劇、曾參予賈樟柯《山河故人》製片人工作的魏軍也有憂慮。
“想讓更多人看見過去西北的情況和現代人之間的感情關係。自己不必須被遺忘,或是隻存有我的記憶中。”《日光之下》最初的劇本創作,與梁鳴對家鄉變化的察覺到是同步出現的。
但他與鄉愁的到達之行,仍在繼續。張大磊正在籌備的兩部影片,都與《蓝色列车》中的人物有關,他想呈現出這些人是從哪裡來的、要到哪裡去。
但20年間,內蒙古海南藏族自治州的音樂創作特徵已出現關鍵變化。德格才讓說,過去,錄音機是一個很關鍵的載體,農牧民們沒有互聯網和電視節目,只能通過傳統渠道聽自彈自唱賽事,堅讚的原型就曾在那時家喻戶曉。
“鄉愁,是與生俱來的”
德格才讓說,影片是以時代更替下他他們的親身經歷為藍本。
谷溪、谷亮和天正,短暫地構築了一個完整的家庭。/豆瓣《日光之下》片花
《八月》的故事情節出現在上世紀90二十世紀末期,烏魯木齊開始進行國有單位轉型,少女小雷在經濟發展革新和家庭發生改變間懵懂成長。“這是在找尋更貼近他們和家庭,屬於一代人的鄉愁;而續集《蓝色列车》的鄉愁更個人化。”前者講訴馬彪獲釋後,返回冰天雪地中的庫村找尋昔日情人卡琳娜,卻再度陷於爭鬥。
畢贛的《路边野餐》、顧曉剛的《春江水暖》、梁鳴的《日光之下》、張大磊的《八月》……近幾年,不論是在影片市場還是在各大影片節,以80後居多的青年編劇們,帶著頗具家鄉記號的影片而來,並總能給觀眾們驚喜。
《蓝色列车》中的主角馬彪獲釋後,返回冰天雪地中的庫村找尋昔日情人卡琳娜,卻再度陷於爭鬥。
2020年10月15日,陝西平遙,影片發燒友戴著口罩出席影片展。第三屆平遙國際影片展於10月10日至19日舉辦。( 圖/視覺中國)
張大磊說,不論是《八月》還是《蓝色列车》,通過影片所作的表達,始終與他們的鄉愁相關。
2002年左右,他還在西寧上學院,當時西寧汽車站的音響系統產品銷售店裡,蒙古族女歌手的卡帶單曲一兩天就換一大批新的,出單曲在當時的教區成為一種風潮。
雕琢六年,投資幾十萬,結果卻如此落差,公映第四天時,《日光之下》編劇梁鳴已將他們的新房子掛到了網上販售,“希望未來還能繼續堅持創作”。
他所言的真正思索,是從2018年電影劇本贏得投資、正式籌拍開始的。
他記得,《日光之下》在比利時公映,放映完結步入溝通交流環節時,有個外國男孩問梁鳴:“為什么會想寫這種一個男孩的故事情節?我覺得就是在寫我他們。”不久前,梁鳴在網上看見一個西北網民寫的電影觀後感,其中提及,電影中所牽涉的故事情節和大背景,在他的頭上也幾乎都出現過。
文章標簽 路邊野餐 春江水暖 花 山河故人 八月 他與羅耶戴爾 熱血街舞 春風沉醉的夜晚 藍色列車 中國新說唱 日光之下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