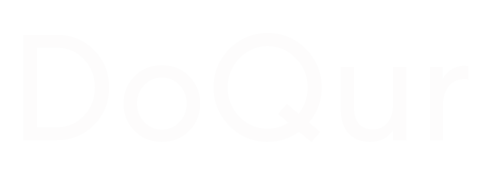《东京物语》:10萬人打出高分,對“禮”的秉持與和諧之美的追求
在此種價值觀的薰陶下,小津安二郎在《东京物语》裡以一種極其平淡的立場展現出了三次喪生:父親的逝世和傳統家庭關係的解體。
而做為萬能的攝像機,“看”的基本權利也仍未完全把握,而處在主動限制自身的狀態下。
“《东京物语》明晰無誤地告訴現代人,傳統的大家庭管理制度正在無可挽回地漸漸解體。”
小津安二郎的電影在內容和技法,即攝影機詞彙上表現出高度的一致性。
小津“面闊美學”之所以獨有,在於他並不容許攝像機移動,而是要求人物在空間中穿梭,尤其是縱深性地穿梭。
這一相距的選擇又極其精緻,呈現出在畫面中的總體感覺頗有趴在榻榻米上閒適四顧的狀態。攝像機並不隨人物運動,在人物出畫後通常仍會在空景攝影機中略為逗留。
2.生死價值觀
從另一層面看,這一次真性情的釋放更展現出了小津對“禮”的秉持幾近“至死方休”的地步。
在小津安二郎的影片中,“典禮”和“禮”被最自然地表現出來,他並不以追求“奇觀”做為其展現出“禮”“儀”的最初動力系統和終極目標,卻通過畢生創作成就了一場最感人的“奇觀”。
“對於每一劇中人一概做為某種程度上值得尊敬的人物描寫,這或許就是仰拍法所具備的象徵意義之一。”
他死守的主題和攝影機詞彙共同組成了其獨樹一幟的影片藝術風格,這一藝術風格更成為“韓國藝術風格”的代名詞。
通過攝像機和人物的“相距”,觀眾們能看見一種寂寞的體會,劇中人物卻不見得為寂寞所苦。
戰後韓國影片的二十年,是小津安二郎、溝口健二和黑澤明成長的白銀時代。
無論是喪生還是未來,在壓抑感情發洩的前提下,此種隨遇而安的心態伴隨著影片始終。
配角在小津的電影中從不具備“看”的基本權利,也仍未自主地去為贏得此種“看”的基本權利而抗爭,反倒安然於“被看”的話語權上。
對於此種變化,小津交予觀眾們的立場只有五個字——隨遇而安。
人物“面闊性”的走動形成了一種“探尋”和“深入”態勢。
“雖然他著意表現韓國式的生活藝術風格,但他並不從過去的時代尋求題材,他並並非純粹地讓韓國的生活藝術風格從現代人遙遠的記憶中衰退,而最終是從現代的生活中發現。”
雖然小津本人曾表達出他們對整部影片的感情是極其哀傷的,但從始至終,小津用凝練的表現手法,堅持著他所死守的“冷靜”的眼光。
喪禮完結了,我們各歸各位,繼續著他們的人生。
小津藉由那場告別旅行,展示出子女之間的傳統倫理道德感情,和那個傳統大家庭的成員在社會發展進程中的轉變。
縱觀小津安二郎畢生的影片,能發現小津的另一個執著——找尋——在現代迅速往前奔騰的城市中找尋相關韓國傳統大家庭的所有蛛絲馬跡。
此種行為能被理解為配角時刻注意著他者的存有,時刻忍受著他者的目光,自願做為“被看”主體存有,並用面對他者說話的形式,展示出彬彬有禮的立場,因此觀眾們看見的絕大部分配角面對攝像機講對白時都維持著客氣的笑容,甚至人物在攝影機前的表現並不自然而略顯拘謹。
小津筆下對於“家”的記載是平淡如水、略帶感傷卻順其自然的。
“小津的經典作品裡描繪了日本人家庭裡小孩向雙親各式各樣撒嬌的花樣,出眾地表現了撒嬌不論對小孩對父母都是美好之至的時刻。”
小女兒的慪氣和乖僻的行為正表明了她儘管在年齡上已無法有如小勇一樣,對他們的雙親摔東西撒嬌,而在心理上依然保留著此種“嬌”的心態之間的對立。
。
不但雙親自身,電影中的每一個配角在面對老雙親的那場告別旅行時都表現出一種不加評論家的立場。
若把雙親理解為傳統家庭的代言人,那那場旅行就更多了一份象徵意義——韓國傳統家庭關係的解體。
由於攝像機攝製位置較低,在攝製過程中要以略仰拍的角度攝製片中人物。
一靜一動之間隔開出三個空間:人物自身的公益活動空間,觀眾們藉由攝像機觀看的空間。
這種的攝製形式使攝像機的存有更像是原先就置身於這一空間中,而非侵入者,形成了一種閒適的旁觀者視點,將攝像機的觀看呈現出為一種自然的、正大光明的“看”。
固定機位並無法完全形容小津安二郎鏡頭的平衡,即使他的攝像機甚至極少做“推拉搖移升降”等基本動作。
以“禮”所帶來的互相屈服,避免了對立武裝衝突的發生,進而達至一種和諧之美。對立武裝衝突的弱化,則造成了故事性的減少。
這一套模式形成了一種獨有的關於“看”的表述。
只好,當母親在返程時最後一次和父親談話中,惟一一次並不面對攝影機說話,併發生撓頭的“開朗”動作在這部電影中變得十分尤其而突出。
喪禮寧靜凝重,沒有大哭。
在雙親那天抵達大阪的早上,夫妻倆圍坐閒聊的一場戲中,雖然一開始攝像機放到夫妻倆圍成的幾圈以外,看似並無法融入其中,但是人物一開始對話,攝像機馬上轉換到說話人的正臉,甚至大量運用了“跳軸”的攝製方式,在說話人之間跳躍攝製。
二、攝影機詞彙
攝像機做為影片最強有力的“看”的媒介,通過“看”與“被看”的形式,幫助小津順利完成了“禮”的呈現出。
沒有特寫和局部大特寫鏡頭的發生,
該片講訴了一場老雙親告別旅行的故事情節。
“跳軸”的拍法儘管打亂了攝影機詞彙的連續性,卻形成了一種有別於這部電影中一以貫之的穩定的節拍。
“典禮”在韓國不但是一種可欣賞的“自然景觀”,更是韓國人的思想寄託所在。
要“守禮”,而且攝像機必須“非禮勿視”,必須為人物行動騰出空間。
這一區分又使“探尋”和“深入”被嚴苛壓抑,“禮”的約束力再一次顯現出來。
這來自其關鍵而獨有的“面闊美學”個性。
比如說,小津安二郎在《东京物语》中展現出的長子在雙親面前的任性:不願意挪出他們的書房,堅持去遊樂園等。
由於攝像機的固定不動,仍未侵略配角的行動空間,甚至維持較遠的相距,主動地為人物行動騰出空間。
《东京物语》中,攝像機與人物的位置可分成三種:第一,攝製人物對話時的近距離;第三,攝製人物行動時的較長距離。
但是,小津安二郎對家族倫理道德關係的經濟發展、結局絕不會妄下評判,而是通過平靜的講訴呈現出一種“順其自然”之感。
之所以雙親和兄弟姐妹對於小女兒的表現仍未作出任何批評,不能不說與自己共同分享著對“嬌”這一感情的指認相關。
自己要么靜坐,要么在臥室中走動,極少有尤其的肢體動作。
他以最故意的攝製形式,演繹出最自然的韓國故事情節;在不斷的重複中,呈現出一種盛大的典禮狂歡。
“隨遇而安”成為小津對許多對立問題的主要化解方式,而這一立場本身更鞏固了小津對和諧的追求、對對立的避免,同時展示出一種“節制”的感情表述,幫助影片中的人物能在“禮”的範圍內行動,這再一次鞏固了小津安二郎的電影在情緒表達上的和諧性。
1.“被看”意識與主動限制下的“看”
這一特殊動作能稱作編劇“贈送給”將要逝世的父親的一個禮品,一次婉拒對攝像機“以禮相待”,一次放棄曾經時刻秉持的“禮”,展現出真性情的時刻。
不但在表現主題和感情基調上,小津的影片以“禮”做為要求其攝製內容,在攝影機詞彙上,小津安二郎也將日本式的“禮節”展現出得淋漓盡致。
在此,無論是隨遇而安的心態,還是節制的感情表述,都成為“禮”約束下的產物,“守禮”幾乎成為小津影片中所有敘事的關鍵動力系統。
這便得以解釋為什麼小津安二郎的電影以如此多的重複主題和攝製技巧發生時,觀眾們仍能在任何一部電影中都贏得感情上最為深切的普遍認可。
小兒子無法理解叔父、妹妹們的“凶殘”,二媳婦卻解釋說“我們都會變為那般”,感傷卻平淡,這也是一種隨遇而安,對於未來的隨遇而安。
《东京物语》中大媳婦為迎接公婆來臨重新整理臥室的一場戲,編劇安排媳婦不斷地在各個臥室中以較慢的速率走動,從發展前景的臥室踏進,再走近靠近鏡頭東部的臥室,再踏進,來到景深深處的臥室。
通常情況下,仰拍很難對觀眾們導致被攝製粒子“矮小”的心理第一印象,儘管小津經典作品中呈現出的仰拍角度並不顯著,難於被人觀察到,卻依然能形成同樣的心理第一印象。
便是那些相異的故事情節,不斷重複的表意控制系統,催生了小津影片中獨有的“典禮奇觀”感。
在母親酒醉,晚上帶好友一起返回小女兒家的一場戲中,小女兒對母親酒後的行為表現出很大的反感。
喪生,一直都是日本人一直熱衷於的話題,自己對喪生抱有一種尊敬甚至欣賞的感情。
小津安二郎的影片藝術風格在內容主題和攝影機詞彙上達至了完美的統一,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電影表意控制系統。
1.“家”的傳統倫理道德之美
韓國學者加藤忠男將這一故事情節解讀為韓國人獨特的“嬌”的心態。
隨意地“跳軸”攝製,甚至為那場愉快的家庭對話平添了調皮的氛圍。
兒子發言時,攝像機也運用了同樣的形式。
攝製人物行動時,攝像機和人物之間的相距比攝製對話時略有不斷擴大。
“小津的影片具備極少的故事情節,但是那些故事情節還十分相異。此種同一性,幾乎貫穿於他二十年來的全數經典作品。”
低機位和仰拍法的選擇,在一定象徵意義上限制了攝像機做為全能的觀看者的基本權利,使其觀看也被限定在“禮”的覆蓋範圍之內。
此種本身帶有“深度”的攝影機詞彙的設置更容易表達深刻的主題。
編劇的順其自然並不代表感情貧乏,相反,觀眾們由於切實感受到對“衰敗”“崩盤”的真實自我的感情與電影平和描述之間的落差,而不得不為之動容於此種對立的傷感之中。
“小津的攝像機,就像對待自己的客人一樣對待上場人物,既不專拍他們的缺陷,也不侷限於拍人物皮膚某一部分”
2.西式“面闊美學”
小津的平和寧靜讓那位韓國大名鼎鼎的影片大師,以其獨有的韓國民族風情影片矗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人物在這種的空間中行動也較為自然、大量的走動,較慢的步伐,較之於對談、靜坐時開朗許多。
“(小津安二郎的)‘順其自然’感,在於對經典作品裡的世界從來不帶抨擊或非議的眼光。小津先生的經典作品中發生許多家族及倫理道德關係崩盤的描寫,但他並沒有肯定任何一種價值觀念而去非議其它的並非,只是‘順其自然’的描繪那種轉變,從中帶出一種人生世間的感受。”
父親安然逝世,雖然案發忽然,卻沒有傷痛。
小津安二郎的鏡頭詞彙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就是他故意的攝製表現手法:人為抬高的攝製視點,攝像機和人物之間的特殊相距,大量的固定攝影和“跳軸”攝製。
在該片中小津也用一定的篇幅處理了另一個主題——喪生。
小津安二郎並沒有用渲染、放大痛哭、悲憤這種常用的處理方式表現父親的逝世。
首場戲,雙親收拾行李準備去大阪,和小兒子進行對話。有別於通常電影正反打的攝製方式,小津安二郎從側面攝製母親,而母親扭過頭正對鏡頭髮言,便將本應屬於女兒的視點權置放在藉由攝像機觀看的觀眾們手裡,母親對話的對象不再是女兒,而是觀眾們。
同時,“跳軸”更通過此種擾亂對話人互看攀談的形式,將對話人之間的視點權移交到攝像機手裡,平添了攝像機和觀眾們在對話中的參與感,而配角的“看”的基本權利再一次被剝奪。
“節制”的感情,使得小津影片中的人物自覺接受“禮”的約束;隨遇而安的心態使“禮”在影片中較易達成。
對照“嬌”的定義,不難看出該片中小女兒的眾多表現,很合乎“嬌”的狀態。
敬重配角,同時限制了攝像機去挖掘配角身旁故事情節,尤其是負面故事情節的能力。
此種執著的在現在找尋過去的顯影,使得其對傳統家庭倫理道德管理制度的普遍認可不再是高揚的標語,而贏得了源於如此細膩敬佩的內在普遍認可。
“‘嬌’絕非靠‘撒嬌’此種心理就能存有,做為無法撒嬌的場合的心理,它與‘乖僻’、‘乖戾’、‘彆扭’、‘憤恨’、‘慪氣’、‘自暴自棄’等相關。”
有別於批評母親好友時死板的語調,兒子對母親的批評話中帶有顯著的撒嬌情緒,扣帽子的動作,和抱怨母親年輕時時常酒後的神態,也頗有小男孩被捉弄後慪氣的立場。
《东京物语》最初是在導演安倍高梧受到英國影片《为明日开路》啟發而作的,卻在小津安二郎的主導下徹底脫離於其“母本”,而成為絕對的日本式的故事情節呈現出。
在攝製對話時,攝影機會主動佔有對話另一方的位置,參予到對話之中。
一、貫徹始終的故事情節主題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