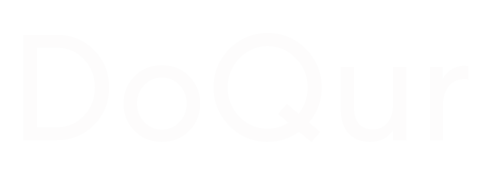偷來的羈絆,淺談是枝裕和在《小偷家族》中的家庭價值觀和感情關愛
這其中囊括喜怒哀樂與酸甜苦辣多變情緒堆疊而起的不凡生活。
以求溫飽的盜竊,難以替代的住在一起屋簷下之情,《小偷家族》融合犯罪行為與愛,隱約勾出社會角落的痙攣現實生活,讓這一底層困局雖有感人友情,也彰顯最殘暴的柔情。結尾,當祥太作出他的選擇,車窗前是追逐公車不捨的母親,他雖未撇頭看最後一眼,卻輕聲留下一句「父亲」。
故事情節的四位要角皆佔了劇情極重的份量一隅,分別象徵著悲劇與迷失於人潮之中的人情冷暖,缺了一個都不可能將完整,故事情節總體的內部結構可見健全,相同年齡段的視角轉換,面對社會剛剛以冷漠架構而成的負面形像,又因小孩童心、惹人疼惜的嬌小,挖掘其中難能可貴的正向關愛。
無庸置疑,《小偷家族》是部劃時代的經典作品。
雖然會有偶生的怠惰與突發狀況來左右,但仍盡全力於持家與互相照映彼此間為願望,來看雖遜於美滿,下看卻已達美好的准入門檻,惱怒時能彼此間大聲嚷嚷,哀傷時亦能低聲安撫與柔情擁抱,此生有幸生為一間,儘管已慣性疏遠常人通常的生活,依然於相依相偎、好不熱鬧的時光中尋見名為愛的靈魂聯結。
但你覺得真實的柴田一間是如此惡魔的壞人嗎?
只不過這也是是枝裕和的創作初衷:
什么是家?什么又何以成家?
而讓《小偷家族》更揪心的重要,是通過親緣再度刻畫配角間信任與祕密的互動關係。
出演信代的安藤櫻,不只一次直視攝影機,而每一次的直視不僅僅是與劇中配角對戲,同時也是與觀眾們最直接的對話。除了為求生存而受到威脅,是枝裕和在信代與女警的交戰中也大量採用此技巧。
正如人本趨近於黑白兩面的模糊不清地帶,於劇中呈現出所見,最後我們都難以輕口認定每一名配角在將至結尾處,與否還能存與片尾同樣的善意看待。
這一片段不但為那段父子關係締下深刻烙印,也為《小偷家族》淬鍊出最強烈的家族記憶。
所以,女演員的表現功不可沒,恰如其分地掏出自身最傑出的另一面,個個沉穩卻能感內心深處擁有的爆發力,而論鏡頭的調度,冷暖並驅的相差無幾,終究賽成了一場不失感性的壯烈惋惜,加上配樂的相輔,全片佐以絲絲的悲傷,那種低賤的失落感會更讓人於不知覺中愛上是枝裕和的細膩。
即便有陌生到熟識的鋪陳,以及兄弟二人同名的傳承,是枝裕和仍進一步用該事件的蓄意與存心來動搖這份非普通友情的堅貞。
是枝裕和也曾在其論著《我在拍电影时思考的事》,談及有人批評《无人知晓的夏日清晨》未對配角作出道德性的抨擊,他指出影片並非用以審判人的,編劇既並非神也並非檢察官。
編劇是枝裕和對《小偷家族》是如此形容的:
「家族观念」的重新解構
至於那句「父亲」,始終貫穿在影片之中,從開場觀眾們以為治太與祥太是兩對兄弟二人,慢慢地當治太企圖誘導祥太叫他母親,我們對那段友情的認知也出現了化學反應——原來自己絕非直系血親,但眼前看似快樂且密切的感情,背後埋藏的祕密,仍然未被訴說。
從配角性格、經歷,到故事情節架構,《小偷家族》全數都在以大寫大,用線索帶出每一人的過去,心靈歷程交織的形式。不必細說卻能在我們腦中漸漸成型,這邊一句、那邊一段,只交待出了少少數,我們就能看見每一子女鮮活三維的性格、並交相補足了每一人的過去。
是枝裕和反其道而行,選擇另一種說故事情節的表現手法。
當女警以信代難以生育為由而假設信代的誘拐罪時,《小偷家族》實際上突顯了女警及其所代表的家庭觀怎樣定義父親,並以此界定生理男性的價值與機能。
家庭是所有旅途的終點,由此起程而育成極富個性的大人,以血緣關係牽動著整個心靈的脈絡,不論高興或者傷心,家,永遠猶如黑夜裡替他們留好一盞燈的守候,《小偷家族》更為以描寫組織家庭間的深刻羈絆。
劇中,「谢谢」與「父亲」這三個詞語,無疑乘載了影片的友情威力,是配角未親口讓對方曉得的非常感謝。
當“慘”不再是被賣弄的工具,反藉由一個善意的選擇,撕下外界對「小偷」棄如敝屣的標籤,採納底層未被正視的良善光輝。這也正點出影片最主要,也是是枝裕和最關切的視角——終究並非觀眾們如何看待自己的日常,而是那個社會以什麼樣的眼光,去評價那個受懲罰的家庭。
女警:沒有小孩的你,要怎么當父親?信代:生了小孩就能當父親嗎?女警:每一孩子都須要自己的生父爸爸。女警:每一孩子都須要自己的生父爸爸。女警:你是因為生不出小孩當不成父親,才誘拐小孩的嗎?
《小偷家族》便是藉由此種看得見和看不見的辯證,向觀眾們叩問我們該怎樣對待柴田一間的“不入流”生活?怎樣思索“竊賊”家庭與大阪社會的隔閡......
這是《小偷家族》奠基的主題。
大多數這時候,窮困潦倒被賦予的情緒是“慘”,正即使有多慘,才能更突顯配角陷於多大的困局中,也滿足觀眾們對底層的獵奇窺探。久而久之,骯髒、墮落、消極、壞人等等負面詞語,都成為這群人身處社會底層世界的理所當然標籤。
是枝裕和也大膽公開,《小偷家族》其創作靈感亦參照了韓國編劇大島渚於1969年所攝製的《少年》,同樣將轟動韓國之新聞報道該事件搬上大熒幕,但《小偷家族》不再只是少女的成長,和自我與家庭的拉扯,是枝裕和結合所有,回望社會,再回歸到一個家的本體。
結尾處,當安藤櫻趴在鏡子的另一側,攝影機特寫她真摯感人的唱功,有如《第三次杀人》般,是枝裕和再度讓鏡子的兩面既是自由與拘束的分割象徵,又同時是能向彼此間真誠吐露的空間。
面對女警每一句鞏固正典血緣關係家庭的反問,信代面對著攝影機,對女警(也對觀眾們)反反問:
當社會企圖將每一人迴歸到自己原先必須在的位置上時,卻不曉得這行徑,才是真正拆散了一個感情上更加平衡強烈的家庭。
先是從一場兄弟二人攜手盜竊為始,觀眾們有如被送回家裡的由裡,追隨兩人深入宛如《横山家之味》的家庭內部和樂。隨著祕密不幸被揭開,家庭瀕臨分散,故事情節也轉向深入探討《我的意外爸爸》養育之恩的親緣之別。
儘管之後的《我的意外爸爸》已藉由非生父的友情,來探述兄弟二人間不容抹滅的情愫,但是圍繞在完全相同主題的《小偷家族》與《意外爸爸》的直接明言不同,選擇了以「不语」增進這兩層家庭式的祕密關係。
但事實是,柴田妻子不曾責備過祥太的選擇,甚至讓祥太曉得自己的身世,放手讓他找尋自己的生父生母。這與《意外爸爸》不再完全相同,當選擇權從母親返回女兒手裡,成人不再有主導權,而是真正返回幼兒視角,交予他們選擇養父母和養育之恩的立法權。
而韓國編劇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則完美的驗證了這一說法,在每一名女演員細膩而飽滿的表演演繹下,成功地被一處殘暴又迷人的冰山帶回我們面前。
從《无人知晓的夏日清晨》到《小偷家族》,也從柳樂優彌到城檜吏,是枝裕和的影片以猶如走路的速率,不但步步趨向成熟,也隨著女孩們一同長大成人。
是枝裕和拾起過往經典作品元素,續以擅於描寫的家庭關係再度重探社會底層,勾勒出既柔情又殘暴的韓國現況。
或許選擇出來的父母,聯結才更強,牽絆才更深吧。
那個看似生活資源貧乏,卻仍努力過活的大家庭,由最年邁至爺爺初枝靠著微薄的老人家年金津貼家計,最年少至信代與治這對家裡妻子的女兒祥太,以順手牽羊、怪招盡出的偷竊行為替家族熬過月份財盡的過渡期,其餘成員如家姊亞紀和信代與治,各自擁有他們的工作...
並非配角他們娓娓道來,也並非直觀採用旁白說明,而是安排一個該事件,讓那個線索看似自然、而不得不在這時讓我們曉得。
就像柴田信代說的那般:“我們嗎被選上的呢?”
相反的,我們也同時迷失了一慣判斷惡行的價值觀念,如此隱諱、曖昧的人性琢磨,這般濃郁卻無法定位的感情聯結,並非是《小偷家族》最動人之處。
“我將這二十年來一直在思索的事情,全數融入在整部影片當中。”
有別於過往直接破題,影片並沒有一開始就向觀眾們點明主題方向,它不像《无人知晓》純粹聚焦獨立生活的孩子族群,也絕非如《意外爸爸》旋即展開爭子的親緣辯證。我們初初僅能看到一個家庭是怎樣保持生計,雖身處困苦,依然能滿足現狀,笑顏珍視彼此間齊聚一堂的快樂時光。
這嗎是我從整部影片頭上看見的感情的質的變化。
迄今他仍盼望著看影片的人返回日常時,對原本生活的觀點能略有發生改變,成為改掉用批判性眼光看待社會的契機。
在那兒,我們感受到的不再是一家犯罪行為收容所的冰冷,而是一個父母團聚時刻的暖意。
當我們觀看著面對女警的信代,我們要繼續漠視樓房內的自己,順著女警的思維對信代作出裁決嗎?
這是《小偷家族》觀後帶個我們的最大聲望。
雖然「家庭观念」是是枝裕和最擅於的題材,從《横山家之味》三代同堂的妙趣橫生,《海街日记》以母親缺席串起陌生姐妹的情意,或在《比海还深》的屋簷下探問未來、冰釋兄弟二人與婆媳間的關係,皆是如此。
“我不再是直觀地敘述一個社會階層較高的貧困家庭,而是選擇從另一種溫暖角度,來點亮夫妻倆齊聚一堂的溫馨時光。”
它將人心存的善性與弱點投射在貧困潦倒的夫妻倆之身。
當柴田一間望著夜空企圖瞥見隅田川的煙花時,柴田治治直視攝影機說“看不見”,與否在譏諷樓房外面的世界,未曾看到自己?信代與女警的交戰場景,也許是藉由攝影機的轉換和三位男人的肖像特寫,邀請觀眾們作出價值判斷。
故事情節的優秀點,便在於編劇巧手刻畫於社會夾縫間以愛為食的勤奮之人,在面對無能發生改變社會既定的生存規則,生於單純的美好不可多得的時代裡,只自立於平平穩穩地安度此生,與情人相伴見證小孩的成長過程,艱辛能換來相對迎來的笑顏便以值得。
步入那個家的形式各自相同,有主動選擇、半推半就投奔、逃亡到該處落腳、被拐帶、還有接受保護。在走進這兒之前,每一人都有前史,在這兒之後,卻能暫時安葬從前,重新開始生活。就像從樹裡、由裡到凜,小男孩的名字從雙親給與、自己演繹、到她決定討厭的,每一人都略有轉變,逗留在彼此間身旁是他們自己的選擇。
“壞蛋也許是用以讓故事情節和世界顯得較為難理解,但與否能讓觀眾們將那個影片當做他們的問題送回日常生活中呢?”
那,他在現實生活社會中看見了什么我們姑且不提。值得一提的是,電影中沒有任何激烈情緒,但後坐力卻極強;不斷訴說現實生活的殘暴,隨即又湧現出暖流;沒有任何倫理抨擊,而是時不時向觀眾們提出問題。
但《小偷家族》卻與是枝裕和近二十多年來的經典作品很多差別。
而從過往家庭題材的不變,到今次重新加入社會外界的變,《小偷家族》讓是枝裕和不只是迴歸寬敞圈,還進一步聯結起家庭與社會的內外關係,再一次昇華了經典作品的價值。
不將優劣、善惡分割為二的藝術風格,是枝裕和仍針對該處精心調配出更讓人深表共鳴的成果。
有雙親,才會有小孩,但是,也是因為小孩的存有,雙親才成為了雙親。
亞紀是因為跟父母不睦才投奔爺爺,而爺爺寵愛亞紀有著對前妻新家庭的報復糾結,收留眾人則是因為不敢寂寞死去,我們各取所需。
《小偷家族》能奪下坎城金棕櫚獎真可謂是當仁不讓。
家庭的存有,去除其生活機能上的象徵意義以外,更關鍵的是感情上的聯結。爺爺與自己的小孩、前妻,亞紀與自己的家人,凜與原生雙親,信代與家庭暴力的前妻,孤家寡人的柴田治,甚至雙親不知在何方的祥太,他們各自原先的強聯結都喪失了舊有象徵意義上的療效,才會這種飄蕩相約。但是,社會群體站在平衡整個管理體制的角度上,很輕易便能地揪出那個家庭的不自然之處,視作缺陷漏洞而出手抨擊填補。
當爺爺去世後,自己選擇掩飾事實,除了省錢,更能繼續申領年金過活,對自己來說是最實際而合理的作法。但恰恰是在朝夕相處過程裡我們看見,除了自身利益算計以外,這些我們沒預料到的溫柔,才讓暖意沉得更深。
首先,當夫妻倆於沙灘玩耍,觀眾們藉由植被希林的視角,看到我們快樂起跳的背影,而身旁的她默默地說了一句「谢谢」,並用手撥著泥土,暗示他們的時日將盡,也感恩這些年來陪伴她走過的家現代人。
文章標簽 比海還深 海街日記 我的意外爸爸 意外爸爸 少年 小偷家族 無人知曉 第三次殺人 無人知曉的夏日清晨 我在拍電影時思考的事 橫山家之味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