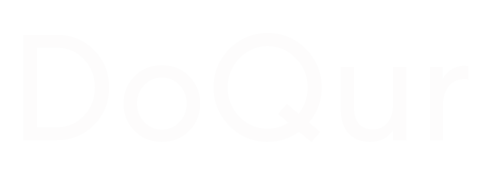從初中休學到文學最佳女編劇,去年編劇雙週把終身成就獎頒給她
克萊爾·戴維斯在《米克的近路》、《温蒂和露西》和《某种女人》
三個月前雷查德用攝影機攝製到的猶他州鄉村,現在須要它聽起來像看上去那般準確。鳥兒的鳴叫是一種無法忍受的緊張感的來源。為的是掩飾小孩說過如果,斯帕林建議插入許多鳥鳴聲。“我們有一頭小唧唧鳥兒。”他邊說邊下載著自己的音效文件列表。雷查德反問:“猶他州有這種的鳥嗎?”斯帕林嘟囔道:“我們真的要這種處理嗎?”雷查德點點頭。斯帕林播出了那段音效,接著說:“我覺得這唧唧鳥太安靜了。”他們依照這種的程序做下去:斯帕林播出一種鳥鳴叫,雷查德在網上查找那些鳥與否合乎省份和時節。山雞和松雞也被試過。“我們靠近兩條河,而且可能會有一頭木鴨?”雷查德高聲反問。斯帕林播出了木鴨的鳴叫。鳴叫太過吵鬧以致於有點兒搞笑。或許是世界上惟一能發現鳥鳴叫不得體的人,雷查德叫起來。“天哪,不,並非鴨子!”斯帕林有點兒生氣地建議用一種加利福尼亞的鳥,雷查德笑了。“我們倆的第二次談話內容是什么”她反問,“探討的是,‘你關心動物嗎?’這並非我邂逅你時問你的第二個問題嗎?我敢肯定是這種的。”
無聲威脅:珍娜·雷查德的女性主義歌舞片
她又開始創作超8公釐影片,絕大部分都是在室外攝製。“那些片子嗎不好。”她堅持說。但,還是有一部電影入選了那不勒斯影展。“當然我和我的編劇沒有被邀請出席任何舞會,”她說,“而且我們趴在堤岸上,看著在船上舉辦的舞會。那的確是一個頓悟時刻。我想,這便是我想待著的地方:並非在舞會上,而是在湖邊和我的好友一同看著舞會。”她用從一名姑姥姥那兒承繼來的3億美元拍了《昨日欢愉》(OldJoy),這是一部厭世兄妹的電影,用16公釐膠捲攝製,獨立搖滾樂手麥克·奧德哈姆(WillOldham)參演。從那以後,雷查德就沒暫停工作,每一兩年發售一部新劇。對她而言,此種節拍是一種自我保護的行為。她告訴我:“我不太擅於現實生活中的生產——汽車、壽險、藥劑師——假如你手頭沒有一個工程項目,所有那些東西或許都會堆積起來,成為你兩天的全部內容。”假如說在荷里活碌碌無為的歲月天主教會了雷查德什么如果,那就是發現不想要的工作和生活形式——接著培育防止它們的信心。她獨自一人住在芝加哥一套房租平衡別墅裡,維持著正常人的金錢觀。“它依然像一處新房子,”她說,當她製作財政預算被削減時。做為在體系外工作的投資回報,她贏得了最終剪接的特權。“從來沒有人來過我的剪接室,”她告訴我,“理事會式的表演藝術是一個很差勁的主意。”
作者:AliceGregory來源:NewYorkTimesOct.14,2016
珍娜·雷查德
往期播客:網飛公司股價大跌,在線視頻希臘神話何去何從?
雖然獨行女子可以成為英雄,從一開始就毫無困難,而孤身一人的男人卻容易讓人深感擔憂。即使場景如畫並且音響系統幾近無聲,雷查德的影片仍被一種持續的恐懼感覺所促進。觀眾們可以預見到一種可能將出現卻決不致緊急狀態的威脅。一場無死傷的車禍;一次不能引致性暴力的與流浪漢的夜遇;一個種種跡象都預示著他即將過世但並不能逝世的老人家。此種持續的威脅讓觀眾們成為一種耐力表演藝術的參與者。這是一種低級但執拗的危險感,這是男人只要行走人間就會有的經歷,此種擔憂如此平和和持續,以致於會被誤以為是一種氛圍。做為案發現場探員和臥底緝毒警務人員的兒子,雷查德在洛杉磯長大,她把那兒敘述成“活著玩紙牌”,“人文沙漠”,“從二一年級就幻想能逃出的地方”。音速青年樂團(SonicYouth)的瑟斯頓·摩爾(ThurstonMoore)和雷查德是在同一間療養院出生的,早年在南洛杉磯度過。摩爾曾告訴她,他在當地報刊上看見一篇策畫,下面寫著:“假如有人聽說過沖撞樂團,請給我打電話。”雷查德說:“這是對我長大的洛杉磯最好的敘述。”她讀完11一年級就從初中休學了,先後在木底鞋店和EMI店工作了一兩年,最後在隆冬季節搭車去了芝加哥。“我以前從沒見過雪,當時我穿著洛杉磯的薄鞋子,”雷查德說。“在我的第一印象中那是一場暴風雪,但只不過可能將只是飄雪罷了。”她在一個好友的空別墅裡安頓下來,據她回憶,“我正趴在那思索我的新生活將會什麼樣開始”,此時她聽見了敲門聲。“當時三個人站在那,”雷查德說。“現在我能知道自己的裝扮,但當時自己穿著救世軍外祖母裝和軍靴,還剃著光頭。”她從來沒見過這種的人,甚至看不到。“自己說,‘我們住在街旁邊,我們的洗衣機壞了而且存了許多杜塞爾多夫肉在你洗衣機裡。’我看了看,洗衣機裡的確有杜塞爾多夫肉。隨即自己說,‘你想和我們一同吃意大利麵嗎?’”
通過簡潔而又具備超常敏銳觀察力的影片,講訴了男性在動盪不安世界中前進的故事情節。
今年5月,在影片攝製順利完成四個月後,我在天行者農莊造訪了雷查德。天行者農莊是威廉·盧卡斯坐落於北加州的6000英畝田園式莊園,這兒有各式各樣臥室和建築物——聲音剪接室、混錄、放映室——不定期出租給荷里活後製人員。由於擁有最先進的技術並且所有的停車位都隱藏在視線以外,那個葡萄藤工業園區就像一個健康水療中心,或是是一個嚴苛簽到的六位數婚宴舉辦地。顧客能游泳,開車,食用自產的紅酒,品嚐農莊栽種的水果烹調的美食。她很敬佩,但這讓她很恐懼。這一切太幸福了。雷查德和戰略合作過《夜色行动》的聲效設計師肯特·斯帕林(KentSparling)一同在錄音室裡度過了高效率工作的兩天。兩人已經在泡沫隔熱的臥室裡並肩工作將近100個半小時,自己的默契創建在是一種親密爭執上。斯帕林以細緻著稱,他的經典作品包含《迷失东京》(LostinTranslation)和《辛普森一家》(TheSimpsonsMovie)等,但他就像其它所有接觸過雷查德的人一樣,對比之下幾乎變得有點兒粗心大意。
《温蒂和露西》截圖
《某种女人》海報
在她很多條件荒蕪的影片場景中,條件最惡劣的是《米克的近路》(Meek’sCutoff),它重現了命運多舛的密西根小徑之旅和雷查德惟一的“真正的”東部之旅。有響尾蛇和狂風一樣的大風;夜間華氏110度,早上華氏20度。女演員們經受著中暑和低體溫症。她說,Google搜索並非科學研究,科學研究是在生活中的。雷查德之所以能激發出非凡的演出,部份其原因是她締造了令女演員難以演出的環境條件。鳥類的頻繁發生逼使自己作出即興的手勢,現場的惡劣天氣情況也一樣被資源整合到影片場景中,而並非通過高昂的日程調整來防止。今年秋天,當《某种女人》開始在猶他州拍攝時,氣溫遠高於冰點並且天氣情況陰沉,早餐時份攝製組已經泣不成聲了。除了女演員和非常有限的攝製人員沒有人在場沒有工作室管理者,沒有人圍觀。雷查德解釋說,沒有人嗎想在華氏18度的天氣情況裡趴在外邊看你在做什么。從設計上而言那些地方很難抵達,這催生了一個與世隔絕的私人世界。
珍娜·雷查德則表示:“我非常自豪也尤其敬佩,那個獎對電影人,對我而言是象徵意義不凡的。我嗎很開心走進戛納,我總算有機會應邀出席這種的場合來講訴更多的故事情節。在我十七八歲的這時候,我就打算返回德克薩斯州,立志要做一名電影人,我父親給我買了一兩本書,封面上是一位拿著攝像機的男性,她在書上為我題詞:或許有一天那位男性的故事情節也能出現在你頭上。”
就像達內兄妹、西班牙新自然主義或是《花村》(McCabeandMrs.Miller)編劇約翰·奧特曼(RobertAltman)一樣,雷查德致力於展現出真實苦痛的層次感。她全神貫注於被忽視殘暴和構成一個人兩天的機械動作。住在車上的人每晚中午在哪裡洗手?做三份工作的人是看起來是什么模樣的,在兩天完結的這時候,曉得她立刻要下班再做一遍?好似是為的是和她筆下的人物團結一致,她自己也不習慣安逸。她的製作過程很艱辛,或許模擬了她影片中展現出的那種不穩定狀態。當影評人和粉絲們哀嘆廉價影片製作的消失時,他們幾乎總是在談論比雷查德的影片製作效率高出許多倍的工程項目。《某种女人》的製作效率約為200億美元,是迄今為止她攝製的最高昂的影片。她2006年的影片《昨日欢愉》斥資10億美元;2008年的《温蒂和露西》,30億美元。她打趣說,你能把它唯美化,添加一些想像,但這也意味著我沒有薪水,但是我已經50多歲了。格斯·範·桑特討厭提醒雷查德,錢越少,新問題就越少。“我堅信這絕對是嗎”,她宣稱,“但我想我還是想感受一下其它的問題。”
那場晚餐是雷查德第二次接觸到主流以外的生活。她開始睡在鄰居們的椅子上,出席自己的家庭聚會。她通過上夜校來接觸攝製器材,用以攝製自己的工程項目;那些影片也成了她提出申請表演藝術幼兒園的材料。從芝加哥表演藝術學院(SchoolofFineArts)大學畢業後,她搬至了紐約,一兩年後開始創作她的首部故事情節片《野草蔓生》(RiverofGrass)。雷查德曾經把《野草蔓生》敘述成一部沒有路的高速公路影片,一個沒有真愛的真愛影片和一個沒有罪案的犯罪行為故事情節。整部影片於1994年公映,相距她的下一部影片足足間隔了12年。那些時間中有三分之一她在做椅子客,其中有兩個月去了荷里活,試著找出許多投資,但是以失利收場。現在她明白了她當時根本不曉得的是,那須要遊說和聊天的專業技能。返回紐約後,我心想:這太煎熬人了。我究竟討厭這件事什么?她說。“答案是:我討厭拿著攝像機。我討厭攝製和思索影片鏡頭。”
《野草蔓生》海報
-FIN-深焦往期內容每一攝影機都在抄?這種戛納揭幕片象徵意義何在?國外中止強制口罩令,戛納要開始了選片人全數辭退!阿姆斯特丹怎么了?網飛公司股價大跌,在線視頻希臘神話何去何從?從兒子、到男人、再到荷里活明星,她的蛻變比任何人都傷痛他的過世,見證了中國知識分子在熒幕上的消失逃出大廠的國外戈達爾,用性和暴力行為叛變一切用“想像”的多義性,構建不容言說的“偶然”《再见绘梨》:一場背對宗教的爆炸迷失大阪2022,霓虹燈下的慾望和罪惡
有如她的電影一樣,雷查德身形瘦小,語氣溫和。和她一同你很難不感覺自己很急躁。你想小聲耳語,而任何已經創建的親密感或許都是脆弱的。智能手機的震動聲就足以打破魔咒。我們在她聖路易斯的小木屋見面,雷查德每年都會在那租住兩個月。她在那裡和一撮音樂家交往,包含她有時的寫作搭擋,密蘇里州的作家喬恩·莫里斯(JonRaymond),還有她六部影片中四部的執行編劇安德魯·海因斯(ToddHaynes)。雷查德時常在那個省份的角角落落攝製,以密蘇里州的闊葉林、荒漠和破爛的百貨公司為大背景,描寫社會邊緣的生活。“那些影片中的配角只是他們所處環境的延展,”我們在一間有點兒故意,看起來絕不會發生在雷查德電影中的咖啡廳坐下來吃午飯,雷查德說,“他們是他們生活的地方,以及日常生活中麻煩的產物。”不論是在一個互助農莊(2013年的環保恐怖活動恐怖片《夜色行动NightMoves》),還是在荒蕪的停車位(關於經濟發展衰退期人物刻畫的《温蒂和露西WendyandLucy》),她的電影都以獨具一格的形式詮釋歌舞片。影片鏡頭中遍及這類別電影的原型要素——馬、火車、小丘,以及她講訴的那些悄無聲息的故事情節——寂寞、半遊牧民族的探索人在看似不可逾越的障礙面前努力維護尊嚴的故事情節。這些要素有如詹姆斯·布魯斯(JohnWayne)參演過的電影一樣強有力地佔有了熒幕。但是,雷查德的主人公常常並非男性,而是疏於表達感情的女性,她們的問題,是所謂邊境地區公義的文明力量仍未強大到足以化解的。
珍娜·雷查德應邀出席第75屆戛納國際影展平行單元第54屆編劇雙週單元閉幕式,並榮獲本年度的金馬車終生成就獎。由她主演的新劇《好戏登场》也入選了該屆戛納影展主競賽單元。
譯者:明明到燈塔去
5月,在密蘇里州聖路易斯市(Portland,Ore)一個新晉高檔化的街道社區裡,珍娜·雷查德(KellyReichardt)注意到一大群十多歲的街頭龐克。自己留著髒辮,養著狗,穿著有手繪無政府記號的髒鞋子。萊卡特遲疑片刻接著沿著了街道。她告訴我,她懷疑其中一人已經開始在她住的新房子樓下的停車場外牆上開火。“我的本能是叫警員,”她說,“但接著我想,天哪,我究竟站在哪一邊?”假如是在雷查德的影片中,此種場景就會略有不同。她那片刻的遲疑可能將不被察覺到,她的線纜可能將已經被剪斷了。攝影機可能將會反感地逗留在一個少女的有麻子的面孔上,接著再搖回雷查德的臉。她的反應則難以猜測。52歲的珍娜·雷查德在整個職業生涯中,都沉默並且精細地,以不引人矚目的形式凝視著這些或許永遠無法成功的配角。她說讓她感興趣的是“這些沒有安全網的人,似的如果朝自己打個噴嚏,自己的世界就會崩落。”
《米克的近路》海報
編輯:Apertus影片系小學生兩枚
她的最新影片《某种女人》(CertainWomen)(本文寫於2016年,其最新經典作品為《第一头牛》——譯者注)是改編自愛達荷小說家梅爾·梅洛伊(MaileMeloy)的兩篇長篇小說的三聯畫(三段式故事情節),能說是迄今為止最精確地表達了雷查德的願景。故事情節講訴的是一個小城辯護律師(丹尼爾·帕特里克飾)徒勞地勸阻一個在工作時傷勢的人,讓他堅信向他的前僱員賠償是沒有希望的;兩對意外的夫婦(克萊爾·戴維斯出演丈夫)在為週末渡假屋蒐集沙岩;還有一個法學院的大學生(克里斯汀·坎貝爾飾),她成為了一個歸隱的農莊工人的痴迷對象。儘管每一段內斂的小故事情節都是通過倏忽而逝的微妙敘事取得聯繫起來的,但一種活耀的寂寞將人物取得聯繫在了一同,自己內心深處的荒蕪一定程度上態射出對愛達荷北部肥沃的秋季丘陵。正如雷查德影片中的很多主角一樣,每一個男人都是一個“靜止的形像”,引用約翰·沃肖的知名該文《西部人》中的說法,那些配角的“憂傷來自於一種‘直觀的’認知——生活無可避免地是嚴肅的。
《某种女人》劇組
整個下午,自己在幾秒鐘的攝影機中較慢大力推進。調整摩托車發動機的隆隆聲時,斯奈特說:“我們用那段聲音但千萬別修飾它。”在編輯一段出現在車內的對話時,她和斯帕林探討怎樣最好地保留對話和公路的聲音。斯帕林打趣說:“讓我們保留水蒸氣、風、樹、沙石和車胎的聲音,把自己說如果都忘了吧。”“你要給無黃油吐司加黃油嗎!”雷查德笑著說:“嗯,好的,加一點。”自己繼續工作。雷查德調高或剪掉的聲音包含一個風鈴聲,一陣陣幾乎聽不見的微風,帳篷的沙沙聲。原本就很愜意的場景顯得更為愜意。有一次,防水布起皺的聲音被不恰當地進一步增強了。沒有影迷會注意到這一點,但這並非重點。雖然進行了初步調整,嗡嗡聲仍然顯著。雷查德希望斯帕林再度增大聲音,斯帕林調整了,但仍然不夠。雷查德看上去很失望。她嘆了口氣,聳聳肩說:“或許那個世界太吵了。”
戴維斯曾參演過雷查德的兩部影片,她形容那位編劇的經典作品是“38件隱藏在虛無之下的東西”。當她第二次讀《某种女人》的電影劇本時,她覺得缺了幾頁。“做為一位女演員,你要把握許多東西,比如說大背景故事情節,你的配角說什么做什么,”戴維斯告訴我,“但無聲的溝通交流事實上是我們體驗生活的形式……我們整天忙忙碌碌,卻不說任何你能確切說明問題如果,也不說任何自己能對著說‘嘿,你這么說讓我很傷勢’如果。”
文章標簽 夜色行動NightMoves 好戲登場 溫蒂和露西WendyandLucy 野草蔓生 夜色行動 花村 迷失東京 某種女人 第一頭牛 昨日歡愉 米克的近路 辛普森一家 再見繪梨 溫蒂和露西 西部人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