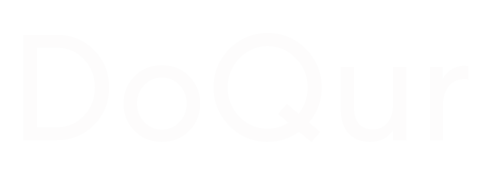像小孩一樣,懷念楊德昌,更懷念那部華語再也拍不出來的《一一》
即使就和當年一樣,Sherry的考量還是在現實生活面,NJ有理想但不曾發生改變,情形和當年沒什么變,重選一次結果自然一樣。
那些境況是多么熟識?自己的人生都不愉快,和我們一樣,也都有許多並不遠大但揮之不去的夢想縈繞於心,也和我們一樣,這是屬於我們的生活,屬於我們的影片。
即使楊德昌創建的並非人物與故事情節,而是整個生活的世界,有如無數的細節之沙組織而成的巨塔,而並非用死板矯揉的對白或該事件,強硬態度大力推進的所謂故事。
撇開電影中吳念真所代表的灰暗美感,裡面最調皮的,必須就是她那兩對兒女了吧,特別是那調皮的小女兒。天真無邪,完全不懂悲歡離合的孩子,編劇卻安排他在電影的最後做壓軸的表演,讓每位觀眾們的心被撞了一下。
這或許是個自我實現的寓言,影射著《一一》影片的自身,與楊德昌的境況。
你能從李凱麗張洋洋頭上看見《指望》裡的石瑪麗和王啟光;
......
即使框中人物強烈的感情,並並非主題,主題是全貌,是一個完整很大的生活世界。那個世界中,劇中人總是在小小地中間,演著戲或者念著對白,而其餘,空蕩蕩的。很的孤獨。
從林孟瑾和陳希聖頭上看見《海滩的一天》裡的張艾嘉和毛學維;
NJ在Sherry關門後立刻敲門,留下一句"我從沒愛過除此之外一個人",在通常故事情節片中這么俗濫的一句對白,在故事情節的鋪陳下卻讓人覺得這是那段壓抑數十年的情感的發洩,毫不懷疑它的真實。
我指出在《一一》當中,楊德昌不只從方式上,採用現實主義的影片詞彙,而內容上,繼承了契訶夫、小津安二郎等人的現實主義傳統,一種真摯的悲憫。
《一一》更讓「出走后的回归」顯現出楊德昌之後未曾表現過的溫暖與溫柔。
讓我較為疑惑的是整部片用了滿多小劇場女演員,大多是演出工作坊的,有劉亮佐、陶傳正、陳立華等等;也有許多我們所熟識的女演員,比如女主角吳念真、蕭淑慎等等。
從柯素雲和吳念真頭上看見《青梅竹马》裡的柯素雲和侯孝賢;
是的,只有曾經活在這樣的時代,經歷過相似的生活的專業人才懂得,此種或許無可挑剔的生活背後,這些無可救藥的孤獨。
而人生的知音、真誠的溝通交流和巧遇迸發,依然讓人清楚意識到詞彙的存有。
楊德昌的影片藝術風格常以「出走」為母題,點出每一配角對自身狀態的恐懼及反感,並非亟欲逃出就是亟欲找尋,卻藉由一個再也沒有體會、也難以表達的老阿嬤唐如韞從昏迷不醒到去世的過程做為取代觀眾們的冷眼抽離旁觀這一切世間該遊戲。
二十多年前NJ即使考進數學系而和Sherry分開,見似可笑的理由,卻或許能完全理解。
荷里活影片中那種剛認識就情話綿綿接著立刻上床的真愛並非我們熟識的,壓抑沉穩的感情才是我們所習慣的,對白少有時候隱藏的情感更加強烈。
《一一》似的“統率”了楊德昌的之後的所有影片民族特色。
無可名狀、無法形諸,但楊德昌用精確的影片詞彙,將這種的生活寫照,捕捉在不朽的《一一》中。為此,所有的觀眾們都必須非常感謝他,非常感謝他願意講訴那個故事情節,即使所謂的關愛或救贖,就寄託在傾聽與描述中。
昏迷不醒的爺爺,單方面地聽著兒孫輩無解的煩憂。
陽陽的話語無人傾聽,也無人能懂,而且他選擇攝影。我想,楊德昌也是這種想的,而且他拍戲。讓表演藝術,橫越詞彙的阻礙,稍解孤獨。
無論是主人公還是小角色,演的都極為出眾。
從吳念嗎老同事陶傳正等人頭上看見《独立时代》的人際社會中真摯與偽善的對照;從吳念真和大田頭上看見《麻将》裡張國柱與柯一正三種相同男權階層或世代的自我辯解或自我反省;
這同樣也是一種寬容。
整部極為精緻的影片,情懷也無比非常大。
《一一》中交織著各式各樣母題,多線敘事平行繁瑣,但又清晰明確,彼此間呼應。楊德昌的電影劇本有如他的構圖,爐火純青。像是詞彙。孤獨的中產階層生活裡,最須要的是溝通交流,但3半小時的片長,甚少溝通交流,但從來不缺少絮絮叨叨的無數詞彙渣滓和難以溝通交流而只更變得孤獨的詞彙。
有如他的攝影機一樣,他總是把人擺到鏡頭中間九分之一的位置,接著用長攝影機與場面調度,替代迅速更迭的剪輯,或者煩膩的特寫、節拍強烈的追隨攝影機。
做為楊德昌的最後一部影片,《一一》就像是一個老編劇滔滔不絕的喃喃自語,但是話講完也就住口了,即使他要說的都已經說完了。
《一一》是一個臺中市典型中產階層家庭的生活,無論是場景、故事情節和人物,都熟識得令觀眾們無比懷念。任何住在臺中市的中產階層,都能借由街頭,找出似曾相識的街景、自身、或身旁親朋好友依稀相異的存有。
即使《一一》的對白太自然太像生活的日常對話,而且每一配角都像是身旁每晚會遇到的人。題材、對話都如此熟識,自然更容易引起共鳴。
楊德昌也老了,而且他懂得此種智慧,而且他懂得,不去揭露與抨擊人性的懦弱與醜惡,即使那太低成本。他不去誇大俗爛地謳歌這些不值得喜悅的所謂戲劇,比如成婚生子,比如成長,比如真愛。而且他不必特寫,也不營造最高潮。就有如現實生活世界中的我們一樣,問題發生,接著,什么也但,最後一切也自然而然地過去了。
營造了整個蒼白的中產階層世界,孤獨與疏遠的困局,楊德昌卻不企圖為自己找出出路與救贖,但也沒有抨擊與攻訐。
從依然持刀捅人的建中青年頭上看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以來的兩性意識與立法權的變遷;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