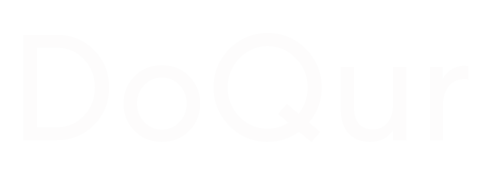《奇迹·笨小孩》是勵志片界的《甜蜜蜜》
與那些極實的人物狀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劇中那無處不在的詩意。
他主動提起《甜蜜蜜》,憤憤不平地說,這就是一部“完全是主動取悅觀眾們到不顧廉恥的一部戲”。我能理解他的憤慨,即使《如果·爱》中男女對於真愛與現實生活的選擇,才是陳可辛真實的內心深處,也是他指出的現實生活。而《投名状》的極端灰暗與恐懼,也是他真實的對兄弟情的理解,對立法權的理解。當他企圖對觀眾們掏心掏肺時,收穫的卻是一盆盆涼水。反倒他們十分駕輕就熟的一部影片, 卻仍然能在若干年後獲得我們不變的歡呼。此種落差似乎會令他惱怒,而且他蓄意貶抑他們的代表作品。
有時的機緣,有時的一點善,溫暖你一生,有時的一點惡,也可能將人逼上絕路。所有人都在這樣的碰面之中,你隨時可能是善的施予者,也可能是惡的製造者。此種對人性的精確體察與把握,讓它還原了我們在那個世界的基本體會,也讓那個通俗的故事情節有了感人的基礎。
文牧野和陳可辛的第三個共通點,在於自己的影片都較為中正平和,既並非那種學院派或是電影節路線,也並非完全的商業路線,自己的影片不憤世嫉俗,也沒有流俗的譁眾取寵。就如陳可辛在某次電視節目專訪中所言的(大意):他不討厭這些大師經典作品,也不討厭這些大俗片,他討厭的是這些處於中間的中等影片。也是此種個性,讓自己對人性從不情緒化,自己都並非從信條、概念去理解人。自己或許天然能理解人性的複雜與多樣,總是能在此種多意之中找出一種準確的均衡,只好這裡頭也就自然地流露出一種諒解和反感。
比如說田壯壯所出演的門房大姐,他頭上所彰顯出的寂寞,讓他收留主人公的姐姐,不止是他的正直。這也是他的須要,你或許能在他看著小男孩時那微笑都化不開的細紋裡窺見他的歡樂。
其共通點,是它們都是所有人共同的記憶,是一切人的最重要的集體關切之一,而且那些故事情節,本身就具備著很強的戲劇化和普適性,總能牽一髮而動全身。深能讓我們深入探討國民性和發展史,淺能撩撥全體國民那多愁善感的內心深處。
此種分寸感,讓那些人物像極了我們身旁的絕大多數人。自己既並非好人,也並非壞人。所有的溫暖,都只是一種物傷其類的憐憫,是一種互相取暖的慰籍。有限度的親情,與有限度的惡劣,親情裡也有著貪婪的動因,惡劣裡頭也有著自己的只好和合理性。
老闆娘同意主人公的方案,所以有他的憐憫,從那個小夥子頭上看見了年輕時的他們,但更多的更何況是,這對他們完全沒有危害。同時還有快點趕走麻煩的現實生活考慮,的話他怎么會只給主人公他部下高管的名片?
所以在這兒,主創人員也同樣表現出了縱容和剋制的均衡。縱容的地方在於,它不吝於去表現那些詩意,對於一個有這種潔癖的製作者而言,常常會覺得那些東西過分俗套和煽情,進而最高限度地採用它們,但文牧野和陳可辛一樣,或許從來都不能有這樣害怕,自己深刻曉得要打動觀眾們是第二使命,觀眾們須要那些東西,讓自己有悲天憫人和自我昇華的渠道。
便是那些攝影機,讓出現在主人公頭上的故事情節,成了一個載體,關於一代人集體宿命的載體,一個關於人生普遍宿命的載體,
整體而言,這是一部傑出的影片,更屬於當下中國稀缺的那種影片,關注中國當下現實生活中庶民的悲喜,敘事成本低卻人物飽滿,圖像能力傑出卻並不炫技,不故作姿態卻又不乏情感,細節都力求到位,但又不流連於這些細節中。所有的東西都在計算之中,卻又將那種斧鑿之氣降至了最高。從某種意義,甚至必須讓許多業內人士自學,什麼樣將一個從故事情節層面並不突出的影片,拍得這么感人。
而此種對於人性的分寸感,便是整部《奇迹》鶴立雞群於賀歲檔的其原因。
當這種一個題材發生時,現代人很難回望當時的熱血,就像所有人都會回憶他們的青春一樣。而對那些受因禽流感等各式各樣重大事件困擾的現代人而言,重返這個充滿著希望也充滿著奇蹟的時代,是一種較好的解壓形式。
它剋制的地方在於,每一次採用時,它又極慎重,決不讓其脫離敘事成為一個單獨的存有。直觀而言,它是把感嘆號當做逗號來用,於不動聲色中,讓你一震,接著當作沒事一樣,繼續低調。此種均衡,讓電影既沒有這種故作的高冷姿態,也沒有那種低俗的媚態。
最後再說一下為什么《奇迹》是勵志片界的《甜蜜蜜》?只不過很直觀,你看看文牧野的上一部戲《我不是药神》,那裡頭對於人性的描摹,對於人在道義與法律條文之間的取捨,在自保與犧牲之間的掙扎,那是一部或多或少能同時展示出光與暗,曖昧與單純的影片,那是有刺和牙齒的影片,而整部影片卻將他本作裡這些難以用是非善惡判斷的所有糾結與對立完全去掉了,只好它也就少了《我不是药神》那種刺到內心深處底層的傷痛,與浴火重生的狂熱。
影片沒有給主人公以倫理上的優越感,而是所有人都是在這種一種棕色的狀態中,這是整部電影真正的正直。
這三個編劇,都擅長表達時代,都能從當下正在出現的變遷中發現這些動人心魄的東西,在大時代與小人物的懸殊對比和對付中,挖掘這些人性的複雜和絢爛。對於陳可辛,它們是《甜蜜蜜》,講訴中國人自改革開放以來,光鮮亮麗出國潮下的那種不為人知的悲歡離散。《中国合伙人》同樣如此,但此次他將目光從社會底層移至了菁英知識分子身上。《亲爱的》,則是對中國屢禁不止的幼兒拐騙的深刻觀察。而對於文牧野首部也是如此,《我不是药神》用一個到巴基斯坦找藥的故事情節,明確了我們曾經有過的恐懼:這些患者所經歷的傷痛,以及懸在每一人頭上的可能將的噩運。
···············
之所以提及陳可辛,第一是覺得他和《奇迹·笨小孩》(下列縮寫《奇迹》)的編劇文牧野都有共同之處。第三是覺得《奇迹》能算是文牧野的《甜蜜蜜》。
簡而言之,廣州和創業,能勾起所有年齡段的夢想,是底層和菁英社會階層共同的集體回憶,是少有的、在那個情緒低靡的時代能通殺的雞血。華強北那個中國硬體創業的君士坦丁堡更是為那個故事情節的真實性提供更多了保障。
劇中這個智能手機子公司的老闆娘和高管也同樣如此。
它們是高空眺望攝影機下,廣州城中村那如蛛網般複雜的公路,是颱風,是大雨中掙扎的蜘蛛和螞蟻,是如雲的高樓下這些飄蕩著的、看著像螻蟻的擦窗建築工人,是主人公在高空窗前狼吞虎嚥他們的便當時,裡頭人也在聚餐的匆忙一瞥。
除此之外,它的地點在廣州。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史的地標性位置。它頭上彰顯著四代創業潮,是八十年代的廣州開放;是九十年代的貧困戶舉家趕赴以東莞為代表的北方,去陌生的衛星城為自己和後裔找一個新的可能將;是2000年後,網絡的崛起,讓大量理工科青年科學知識分子重新深感了科學知識就是力量,他們在那個無人區裡白手起家,成了許多人的歌手,也成了那個時代新興的最大既得利益社會階層。
先說共同之處,主要有三點,這三點讓自己輕而易舉地超越了自己的同行。
《奇迹·笨小孩》是文牧野的第三副部長片。自電影票房口碑雙豐收的《我不是药神》後,那位青年編劇的續集一直更讓人期盼。在影評人梅雪風認為,《奇迹》與陳可辛編劇的《甜蜜蜜》有異曲同工之妙,擅於表達時代與共同記憶,在類別技巧上很突出。而與前作《我不是药神》較之,《奇迹》將“這些難以用是非善惡判斷的所有糾結與對立完全去掉了,只好它也就少了《药神》那種刺到內心深處底層的傷痛,與浴火重生的狂熱。”
同理,是章宇所出演的工頭,他給主人公比他想象多的錢,所以是他的善心,但他也曉得主人公的倔勁,他懼怕麻煩。此種嫌惡卻又感同身受的反感的激戰,是那個人物生動的其原因。
它們是讓電影增鮮的味精,是讓故事情節顯得有人生滋味的鹽,是讓這些真的的細節和情節發酵成滌盪心靈交響曲的酵母菌。它們是主創人員全知視角下施予主人公的這種寬慰,是主創人員忍不住插進去的評論家,是主創人員們的一聲嘆息。
整部《奇迹》也是如此。
先說一段往事,2009年,我還在做影片週刊,專訪了一名編劇,他評價他們最著名經典作品時嚇了我一大跳。那個編劇叫陳可辛,整部影片叫作《甜蜜蜜》。當時他在為他監製的《十月围城》做宣傳,在內地還沒有享受到《中国合伙人》《亲爱的》給他帶來的可觀名利,之後攝製的三部經典作品《如果·爱》和《投名状》,都投入了他很大的心力以及真情,卻仍未獲得應有的市場投資回報。
高管不同意主人公的方案,當然也絕非他的惡意,更何況更多的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慣性使然。他中後期對主人公的些許不滿,也只是他看不慣主人公對他權威的挑戰。而且他沒有促進主人公的事業,也沒有真正阻擾。電影也沒有對那個人物有什么倫理評判,沒矮化也沒有拔高他,他既沒有在主人公成功後假惺惺祝賀,也沒有所謂的內疚,他只是心情複雜地回望了一眼,接著繼續他的工作。他們只是有時相連的陌生人,他有著他自己要操心的事情。
但這也只能當做一種憎恨觀眾們有眼無珠的氣話,作嚴禁真。而且他前面又補充到:“我沒有不討厭那部戲,但我覺得我們把那部戲看得太高了,只不過它就是最通俗的荷里活影片,通俗到你要什么給你什么,要障礙有障礙,好人好事全是好人。《如果·爱》才是生活,才是人性,我拍《如果·爱》就是我個人對《甜蜜蜜》的思考。”
還有嶽小軍出演的庫房老闆娘,和沒露臉的主人公的房主,似乎也不壞,自己都盡全力拖延了對主人公的催款,但此種反感是有限度的,就有如嶽小軍所言的:我也有麻煩。但自己並非劣質影片裡的趕盡殺絕,前面主人公還是順利從出租屋裡取回了行李。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