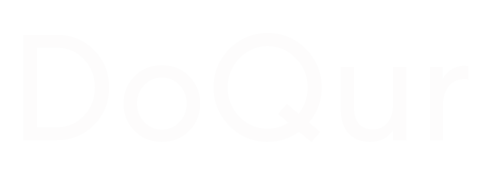李滄東以現代文學的形式,對付人世間普遍存在的遺忘和粉飾
《烧纸》
即便在那個時代,持久地愛一個具體的人,要比愛好人類文明更為考驗人心。
因而,李滄東的影片並不急於頌揚自由民主時代,而是繼續把攝像機投入勞苦大眾,去聆聽自己的憤慨、傷痛,和日益被遺忘的崇高。
貼有社會熱點的寫作,難速朽。在李滄東寫短篇小說這個時代,寫社會運動,只不過是一個熱點寫作,熱點寫作,包含過分貼近現實生活的寫作,要引發聽眾探討難,但要經受住時間考驗,十年、二十年都沒有喪失可讀性,很考驗小說家的筆力。在這方面,李滄東至少寫下了幾篇沒有速朽的短篇小說,比如說《鹿川有许多粪》《天灯》,即使現在讀,我仍然能感受到一種劇烈的痛感,共情人物所面臨的倫理選擇。這說明,李滄東是一名出眾的短篇小說寫作者,他至少寫下了歷經三十年、依然讓聽眾五味雜陳,對生活進行嚴肅思索的短篇小說。
李滄東企圖讓聽眾思索:一個重的生活跟一個輕的生活較之,重的就一定比輕的正直嗎?參予宏偉運動的現代人,自己的人生與否就比困守柴米油鹽的人更有意義?倘是如此,我們又怎樣看待犧牲自我事業、囿於浴室與家庭的現代人?
當鍾秀看見了Ben的生活之後,他感嘆日本的蓋茨比好多,為什么很多人生來就那么有錢,過著愜意而典雅的生活,而很多人只能住在郊野以外。鍾秀跟Ben的對比,是三種相同的飢餓狀態。鍾秀的飢餓狀態是他發現他被固化在了社會的中下層,他很難去逾越卑下的宿命。這是一種化學物質與名譽上的飢餓。Ben的飢餓在於:即使他那么有錢,他仍然在精神上深感空虛,仍然深感一種存有的虛無,以致於他不得不通過燒塑料棚乃至獵捕男人的行為,去獲得一種精神上的滿足。
“所以,珉宇會與世隔絕很長一兩年,但,人生被扣押,卻總要繼續活下去的,又何止珉宇一個呢?那個骯髒的大千世界,已經喪失了所有的純潔和體面,我卻要在這兒生存下去。走吧,他看向黑暗,勸阻著他們。在這片非常大的垃圾箱層上,把所有的髒汙、憎恨,還有這些已經被捨棄的夢想,全數踩在腳底下,走向我那渺茫在半空中搖搖欲墜的十四坪的安樂窩。”
《薄荷糖》與《绿鱼》《绿洲》一道,被譽為李滄東的“綠色四部曲”。它們都以普通人做主人公,呈現出社會轉型陣痛回到一代人頭上不容消除的傷疤。福柯曾表示:“思想病症並非一種自然的或生理方面的病症,而是一種對人群加以分類的社會機能,它的誕生是發展史的產物。”李滄東的影片同樣呈現出患者,甚至是在旁人看存有思想問題的人,但他的著眼點並非對患者的批評,而是對病因的回溯,是什么其原因引致一代人的思想創傷,相同世代的日本普通人,自己面對的失落又有什么相同?
在短篇小說中,李滄東不但嘲諷權貴,也嘲諷了關心遠方卻缺乏自理能力的一派人文人。他在短篇小說中這樣寫道俊植的母親:“自己此種人極為博學,比任何人都深諳世界的運行基本原理,對當時的政治情形或是日本社會的結構性對立了如指掌,三天三夜也說不完,事實上卻連化解兩天一頓飯的能力都沒有。”
在成為編劇之後,李滄東是一名作家,他的長篇短篇小說《烧纸》和《鹿川有许多粪》創作於1980/1990二十世紀,近兩年先後被北京大學出版社鹿書工作室導入中國。李滄東曾自謙道,他們寫短篇小說並不夠好。似乎,做為作家的李滄東,在成就上並比不上做為影片編劇的他出眾。但李滄東的短篇小說依然值得一讀,即使過去了二十年,以嚴肅的表演藝術國際標準看待,《鹿川有许多粪》《关于命运》《天灯》,以及李滄東成名作《烧纸》的同名短篇和《火与灰》,都是構思精緻、值得細品的短篇小說。
在豆瓣評論家區,有聽眾注意到:“在《鹿川有许多粪》中,幾乎每一則故事情節都是圍繞小學生運動展開,但是故事情節的主角又不處在運動中心,他們常常是運動參予者的好友、家人或是老師。”比如在短篇小說《龙川白》裡,李滄東描寫了一個參予獨立運動卻無路可走,給自己的女兒取名為“莫洙”(韓語音同“恩格斯”)的老父親,奇怪的是,當他被日本警方誤以間諜罪抓入牢中後,他沒有伸冤,反倒想要宣稱自己根本沒有做過的犯罪行為。在與女兒會面時,他說:“有個詞叫做‘龍川白’,能指瘋子,也能用以稱謂這些據傳受到上天懲處的麻風病人。總之,是那種與健全人或是普通人合不來,被世界捨棄的存有……細算來,我也算其中一個。”
書中有一段話力透紙背地描寫了日本民主化運動中,有如“龍川白”那般的心理:
《万尼亚舅舅》裡,契訶夫寫到:“我們要繼續活下去,萬尼亞表弟,我們來日方長,還有很長一串單調的晝夜;我們要耐心地承受行將來臨的種種考驗。”而李滄東的經典作品反反覆覆只不過傳遞著一個意志——千萬別那么快放棄你的生活。千萬別輕而易舉,把你的愛好解除武裝於麻木和平庸。
現如今,當宏偉敘事被消解,個體生活浮沉在破碎之網,製作者對生活象徵意義的探尋,更變得彌足珍貴。在影片《诗》裡,老婦人紀子在承載了心靈苦痛的湖泊上行舟,卻沒有發生改變她對詩的愛好。就算生活普通如微粒,她仍然能看到夜空,找尋屬於自己的明星。李滄東書寫獨自一人作詩的婦女,他的經典作品何嘗並非一首首心靈之詩。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寫過一類人物,自己愛人類文明,卻不愛具體的人,在李滄東的經典作品裡,也許真正令我為之動容的是,自始至終,他都沒有放棄對具體的人的追索,他筆下的人物沒有即使困難,也沒有即使醜陋和活著本身的不完美,就放棄愛好具體的生活。
李滄東具備極高的現代文學素質,也有政治學家那般對公共議題的深入發掘,他的影片關注現實生活,富有獨有的意境之美。比如在《燃烧》中,他關心今天的年輕人為什麼深感憤慨與恐懼;在《薄荷糖》中,他借個體敘事和倒敘表現手法,呈現出了社會轉型時期日本群眾的撕裂和隱痛;在影片《诗》中,他又將攝影機對準一個65歲的男人,拍她怎樣去自學作詩,拍一個男人對生活的愛好、對自我與他者生存重負的直面。
比如說《鹿川有许多粪》,短篇小說中,主角俊植是一個其貌不揚的普通人,他年輕時是個小僱員,住在破舊的出租屋,努力奮鬥半生,沒個名堂,掙來的錢也只夠在郊野滿是排洩物的地方購房,“儘管只有23坪”。相比之下,他的兄妹珉宇是大邱學院的小學生,承繼了母親的士大夫個性,面相俊俏,手掌白淨,即使參予小學生運動而借住在弟弟家避開警員。
何為存有象徵意義?這才是李滄東超越社會階層表達,在創作中不斷提出的大哉問。我們如何尋得人生的象徵意義?什麼樣的生活才並非平庸生活?在李滄東的經典作品裡,能夠看見契訶夫的影子,早在一千多年前,契訶夫就通過《万尼亚舅舅》《海鸥》《樱桃园》鼓舞現代人思考平庸生活,去為真正理想、公義、良善的生活作出努力。
而且,《鹿川有许多粪》是李滄東短篇小說手藝的健全之作。李滄東書寫現實生活,但並沒有落入痕跡現代文學的窠臼。它並非直觀的抒情與歸罪,而是致力於呈現出相同的關係、相同的生存狀態,乃至社會悲劇對親歷者導致的精神創傷和後遺症,進而留下一份份具體的“患者手記”,以現代文學的形式,對付人世間普遍存在的遺忘和粉飾。
李滄東並沒有過多現代文學方式上的技術創新,但他對建築工人、小市民、右翼分子、政客等人物的觀察準確而老練,使他徹底擺脫了士大夫寫作常有的布爾喬亞習氣,流露出生活感和抱薪取暖的慈悲。即使日後不再寫短篇小說,攝製影片,李滄東聚焦的主題仍在延續。在臨時政府時期,李滄東關注的是人對極權主義的抗爭、對於公義的找尋,以及社會集體暴力行為(比如光州該事件)對一代人的靈魂衝擊。成為編劇後,李滄東關注的命題更為多元,彼時日本步入民主化時代,一代人的努力獲得投資回報,社會的貧富差距、社會階層隔閡卻仍未獲得化解,反倒在財閥與新保守主義經濟發展的大背景下愈演愈烈。
《燃烧》的主題並不侷限於社會階層表達,李滄東傾訴鍾秀和惠美那些邊緣人的故事情節,探索人的存有象徵意義、真實與虛假的關係,惠美開篇就點題道:“別想著這兒有橘子,忘記這兒沒有橘子就好了。”一個人在社會上的存有,是因為有他者普遍認可他的存有,假如所有人都把他遺忘,他在社會象徵意義上就已經消亡了。
從《烧纸》《鹿川有许多粪》到《燃烧》,李滄東在創作中習慣自小人物入手,通過家庭中的人事,讓聽眾感受到日本整體的社會氣氛。比如《薄荷糖》的男青年金永孝、《绿洲》裡的中度腦麻痺病人韓恭洙,還有《燃烧》裡住在朝韓國境線附近的困苦小說家鍾秀。在他的處女長篇小說《烧纸》中,相似的人物也比比皆是。《烧纸》裡遭受騙局的寡婦母親、《脐带》中的冤死父親和守寡母親,還有《为了大家的安全》中的老太太……自己或是喪失家人,或是因政治公益活動而蒙冤,亦或者,是這些在現代化進程中孤立無援的進城建築工人、宣告破產市民,總而言之,自己因種種原因成了社會底層,是這些我們在聚光燈下極少看見的人。
挑剔的金基德曾說:“在日本,我是第三號人物,姜帝圭排第三,李滄東排第二。”這雖是個人之見,卻可見李滄東在同行中的聲望。在日本,李滄東以富有文化關愛的意境影片聞名於世於業內,而在許多粉絲心目中,他是一名不折不扣的軍人編劇,出生於普通人家,影片主人公絕大多數也是普通人,就算功成名就,李滄東的頭上也依然保留了知識分子和勞工階層這三種個性。
只好短篇小說開頭寫到:
值得一提的是,俊植的雙親形像,和李滄東他們的雙親十分相近,李滄東的父親是參予社會運動的右翼知識分子,他的母親則是一個辛勤度日的建築工人男性,當他的父親為國家前途踏上街頭時,是她的母親經濟負擔起撫育家庭成員的職責。
《鹿川有许多粪》
自己是三類迥異的人,俊植低賤度日而心有不甘,珉宇富有理想卻不擅於生活。俊植像爸爸,一個面相普通、野蠻生存的勞動婦女。珉宇像母親,一個富有富有同情心、關心國家大事的人文人。李滄東沒有偏袒某一方、控告另一方,而是通過二人價值觀的相同、對立的加劇(俊植丈夫對珉宇照料有加,引發俊植怨恨),來表現這個時代日本知識分子與打工族真實的心理狀態。他沒有美化底層和知識分子,也沒有突顯強烈道德感的姿態,他的短篇小說結合對比、嘲諷、暗喻、象徵等表現手法,向聽眾狠狠地闡明出——我們的生活可能將創建在一團汙穢之上。
千禧年以來,日本影片態勢強勁,李滄東、奉俊昊、洪尚秀、樸贊鬱、金基德等都是五大影片節的常客,2020年《寄生虫》獲奧斯卡金像獎,再次將日本旋風推向最低潮。有論者表示,《寄生虫》能夠陸續蟬聯戛納影片節和奧斯卡,不但在於奉俊昊團隊的能力,也跟世界電影界對日本影片的整體普遍認可相關。早於2019年,李滄東的《燃烧》就曾獲得戛納影片節場刊打分最低的肯定,他也是當今世界最被普遍認可的亞洲地區編劇之一。
在李滄東的經典作品裡,憤慨是一個關鍵詞,李滄東表達的憤慨並並非歇斯底里,而是一種根植於人內心深處的壓抑。象徵和暗喻是他的常用表現手法,比如在《燃烧》中,蓋茨比的梗、惠美的表演、燒塑料棚等,都是李滄東埋下的暗示。
《鹿川有许多粪》是一部直面生活汙穢的長篇小說。化學物質的汙穢、思想的汙穢,乃至人性倫理上的兩難,就有如鹿川的郊野,這些廢棄物車揚起的灰塵、被遺棄在地的廢棄物、汙水和鳥類遺體、乃至大片大片臭氣熏天的排洩物。當俊植投訴哥哥後站在排洩物圍困的農地上,李滄東辛辣地表示他那被一團汙穢圍困的生活文件系統的虛無所在,卻同時也向每一個親眼目睹這一幕的聽眾回答——當我們凝視著俊植的不堪,我們離俊植又有多遠?
李滄東住在大邱的軍人區。離該地不遠是江南區窮人的豪庭,同一處衛星城,高牆分開了相同的社會階層。他曾經出任過日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副部長,他們也是知名編劇,但在日常生活中,他崇尚樸素,家中佈置並不風尚。即使是在片場跟劉亞仁、史蒂文·元等明星喝茶,他吃的也是摺合人民幣幾十塊錢的飯菜。
李滄東的經典作品像是一篇篇解剖學調查報告,他以著名詩人之心結合心理學視角,對時代的失語者投射了嚴肅的目光,那並非低成本的反感,也並非影展獲獎的素材,而是一個個具體的人和自己須要被理解的生活。在李滄東的經典作品裡貫穿著一個主題:沒有一個勞動者理所應當被犧牲。一個社會,有人關注輝煌和成就,但總有人要聆聽灰塵、廢墟和沙石。表演藝術並非營造幻夢、快速遺忘,表演藝術應當有底氣直面現實生活、刺破幻夢。更關鍵的是,保有你的毅力和憤慨,在很多這時候,這比天賦更關鍵。
“我說我沒有任何犯罪行為,是在撒謊。我現在才曉得自己犯了什么罪。現在,我要坦自己所犯下的罪。 首先,我指出自己沒有犯罪,此種想法就是錯誤的。我甚至沒有意識到自己從哪裡開始發生了問題,此種愚就是一種錯誤。問題在我自身。 我迄今未曾放棄過自己。即使是為勞動者辦夜校,我對這片農地上的群眾、被捨棄的富人們、我的鄰居們和兄弟們,只不過從來沒有過真正的痛惜和愛慕。我難以對他們的傷痛與憤慨感同身受。我儘管曉得那個社會的對立與惡魔,卻難以與之對付,乃至獻身。對於任何事情,我都感覺不到奉獻自我的熱誠。 我甚至未曾真正愛過父親。我要成為父親的乖兒子,努力學習,報答父親的傷痛與犧性,此種想法自小支配著我。同時,我又不斷地想要逃出父親。我對渺小的東西,就連馬路上一朵花開的花也很吝嗇,難以敞開自己的心扉。”
富豪Ben輕蔑一舊地說:“日本的警員,不在意那些東西的,那些又不行又髒亂得礙眼的塑料棚,自己,似的都在等著我把它們都燒了呢,我看著那些燃燒的塑料棚,會深感喜悅,接著這兒,這兒會深感貝斯聲,從骨頭深處響起的貝斯。”便是這些話讓主人公鍾秀齒冷,對Ben心生憎惡。
文章標簽 為了大家的安全 綠魚 燃燒 天燈 鹿川有許多糞 龍川白 燒紙 薄荷糖 關於命運 火與灰 臍帶 綠洲 詩 櫻桃園 寄生蟲 海鷗 萬尼亞舅舅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