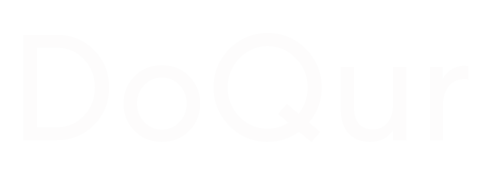《黄土地》:那片厚實的農地,那份深邃的少數民族氣
提到《黄土地》,我首先想到了真正的、廣袤的黃農地,該片攝影張藝謀運用大色塊和色覺強烈的畫展現出了無盡的象中之意以及象外之意。在電影的結尾,大量環境外型營造出了一種獨有的氣氛:那份專屬於延安黃土的少數民族個性。大全景的黃農地千溝萬壑,在夕陽的襯托下變得十分莊重與凝重。在鏡頭的總體構圖中,黃農地佔了絕大部分佔比,夜空與人物不大,用來表現農地之渾厚,使觀眾們更多的發掘黃農地和人物的關係。編劇陳凱歌說:“電影的主旨,並非一般性的講訴一個有頭有尾的故事情節,而是想在更深層次上,對我們的少數民族性進行探索。”在敘事上,《黄土地》既寫實又水墨,電影中既樸實、真實的記錄了延安高原獨有的山川地形和風俗人情,又飽含了製作者對少數民族發展史的深思;在紀實中展現表現性,表現天闊地博、人之宿命,表現出中華少數民族自強不息的思想和人民從原始的矇昧中煥發而出的吶喊和對光明未來的渴求和追求。同時,《黄土地》在熒幕呈現的是一種神小於形的審美觀取向,敘事線索被壓縮,極其簡練,傳統的話劇武裝衝突也沒有進行突出的表現。比如翠巧被逼婚、翠巧和妻子的武裝衝突等那些敘事點並沒有展開表現,非線性的敘事讓坐落於片狀的情緒性內部結構,呈現出澎湃的情緒力量。以此上看,農地上的宿命與農地上的起伏的情緒交疊成為情緒主線,順從與抗爭、衝擊與激進,每一情緒場面都傳達出新的外型信息,使電影的呈現更有震撼力,使觀眾們在農地和人物宿命之間更多的思考傳統人文和少數民族功能。
《黄土地》:那片厚實的農地,那份深邃的少數民族氣
黃農地決定了當地人的生存形式和生存狀態,一方面它撫育了人,另一方面也吞噬了人。像翠巧爹等老一輩人,自己就像是人格化了的農地,自己臉上溝壑般的細紋,和農地一樣壓抑,卻又維持著農地內在的和諧。自己在這片黃農地上繁衍生息,一生背朝黃土,自己遵從著千百年來古老的生產形式,落後的生產力帶給自己封閉守舊、愚昧麻木,就連對聯也用圓盤來替代……但當自己站在黃農地上,卻有難得的熱誠與張揚。憨憨的沉默是承繼父輩“愚昧麻木”的“典型”,父輩們傳遞著古老的“農地神學”,培育一個又一個“憨憨”。但最後憨憨略有發生改變,他的心靈熱誠被喚起,成為一個行動者,這寄予了編劇對少數民族未來的期望。翠巧最初也礙於男權的限制,在電影結尾,翠巧看別人的婚宴時,前面的對聯上赫然寫著“三從四德”,男子被“莊稼人的規範”所禁錮,後變為勇於與宿命抗爭的覺醒者。顧青走進之後,給受傳統倫理道德負面影響的城鎮帶來了文明世界的信息,使“黃農地”煥發惱怒。他不理解這兒古老的生活形式和農地神學,他企圖發生改變這兒,想通過民謠來向外地傳達這兒的“生活現狀”。但他並沒有真正的“發生改變”,他的作法只是起到了非常有限的效果。中後期,顧青的那份厚實、蒼涼的壓抑與無力被觀眾們一覽無餘。在現實生活生態環境的烘托下,那些作法變得極其脆弱與縹緲。
如果說《一个和八个》是第四代編劇的開山之作,那么《黄土地》則是標誌著第四代編劇真正崛起的電影經典作品。《黄土地》改編自柯藍的詩歌《深谷回声》,是由陳凱歌主演、張藝謀攝影的一部文藝題材的電影,整部影片讓觀眾們在熒幕上感受到了強烈的聽覺張力和人文象徵意味。第四代編劇視角有別於以往編劇,陳凱歌將目光投向了肥沃而又有活力的黃土地,通過攝影機把少數民族大災難、現代化進程的艱困和國民性相取得聯繫,從相同層次去探索少數民族精神、傳統人文和人生積澱。《黄土地》是一部追懷經濟發展史、探索少數民族人文根本原因、闡明少數民族個性的詩性電影,具備很高的價值觀深度和經濟發展史寬度。影片中突破性乃至顛覆性的電影詞彙、反思性敘事,對中國文學電影的經濟發展造成了方向性的負面影響。
煙臺師大新傳大學話劇影視製作現代文學2020級2班 張凱悅
《黄土地》於1984年公映,近二十年來,人民生活、思想、化學物質水準都有了顯著的提升,《黄土地》也就有了更高的重大意義。人之人之間的的正直與純真的個性被電影保留,電影不加科技感的修飾,質樸的記錄了延安人的生活,這也便是當今電影界缺少的題材。影片中延安人深深地的愛著這片農地,每一個場景都透漏著少數民族韻味,展現出著少數民族氣節。《黄土地》的電影藝術風格和詞彙形成了一種新的圖像,並深深地的負面影響了第四代編劇晚期的敘事傾向和藝術風格基調。它展現出給我們的是一種宏偉的人文視野,精湛的公理化技巧下滲透出更多的神學與發展史的思索,濃郁的人文韻味和很高的人文品德,是中國電影人文個性的獨有個體的展現出。那片黃農地也許已經變了樣,但你看!腰鼓又舞了起來,那份少數民族氣一直在!
影片的構圖多使用水準構圖,遵從對比蒙太奇的準則。鏡頭中綿延的黃土地佔有大面積,高高的地平線,顯現出來了黃土地的廣袤與厚實,人物則多發生在鏡頭的一角,此種反人與物的構圖突破了舊有的規範,拓展了攝影機的衝擊力。在此種失衡構圖下,人變得較為壓抑與無力,表現了歷史大背景下封建禮教對人的束縛。電影中,看似千溝萬壑的黃土地為“敘事大背景”,且其才是突出的“主人公”。影片中時常看見人做為一個“小點”發生在鏡頭中,所謂“萬綠叢中一點紅”,也是運用的此種對比的美學效果,強化了鏡頭的感染力,更為突出主題。黃土地絕非“敘事大背景板”,而是整個少數民族人格化的象徵體——底蘊在少數民族人文深處的激進個性和難以脫逃宿命束縛的悲哀。
做為第四代編劇的末期電影,《黄土地》具備很強的探索性象徵意義。陳凱歌編劇通過精湛的表演藝術表現手法,把敘事不利因素和暗喻不利因素、抒情和詩意不利因素有機的融合起來,把詩歌的內部結構和詩的意境有機的融合起來,多樣了故事情節,使電影呈現更為三維,達至了電影的創新性象徵意義。《黄土地》中的美感運用拓展了故事情節文件系統,影片美感類型不多,以暖色調居多。想像中,延安高原是黃褐色、蒼白的“蒼涼”,而影片中是穩重而溫暖的藍灰色,此種美感基調賦予了“黃土地”的母性光輝。同時,這有一種模糊不清視象的“舊感”,使“發展史圖像”呈現出模糊不清化的狀態,大片的置景渲染延安的人文韻味,展現出人文意蘊。除了大面積的藍灰色,就以黑、白、紅四種顏色居多:黃色的婚宴行裝、白色的腰巾、黑色的棉襖等莫不展現出當時的少數民族人文風貌,在純粹濃烈的藍灰色中透漏著飽和肅穆。以黃色為例,它通常象徵著奔放、熱烈,但在整部影片中,每次發生都會給人不一樣的體會,“紅”也許是封建制度愚昧的壓榨、衝破束縛的衝擊力,亦或者對未來的熱望,都表達了編劇對傳統少數民族人文有絲絲纏纏的不捨。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