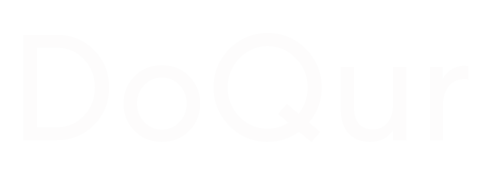獨家|戛納得獎影片《延边少年》編劇後漢書鈞溝通交流分享
我感覺到那些影片傳達的感情是人類文明共計的,它並不受制於某一地域或這種情境。如《小城二月》講訴了一個“兒行千里母擔憂”的故事情節,影片刻畫了一名無時無刻牽掛兒子的父親形像,什麼樣去找尋那個男孩、男孩與否被找出,並並非我們最關心的話劇前提,而是這位父親的真實感情打動了我們。對於這樣規模的影片來說,刻畫一個真實、可信、感人的形像,或許是一個著力點。
那些影片都是在講訴一個大家願意接受的、可信的故事情節。而且,我們希望《延边少年》中女孩的形像儘量的真實可信。只好我們一同探討:我們十多歲時在做些什么事?心底在思索什么?大家溝通交流之後發現,這個年齡想的事情並非去哪裡玩,就是對異性或感情的幻想,這是我們許多主創人員溝通交流之後共計的體會。
做為後漢書鈞編劇三入戛納的首部經典作品,《延边少年》刻畫了真實自然的人物和環境,高水平的圖像層次感突出了人物狀態,這成為編劇之後三部經典作品《野马分鬃》、《永安镇故事集》一脈相承的藝術風格。
您將要看見的是一段歷史記錄。2019年4月17日,中國傳媒大學話劇影視製作學院電影學專業的老師與同學後漢書鈞編劇進行了一場相關《延边少年》及影片創作經驗的分享溝通交流,以下內容摘自溝通交流記錄。
《莱迪》講訴一名剛經歷過生育的貧民區的男性,她一直找尋小孩的父親。在找出小孩的父親後,那位母親與父親趴在一同,她靠在他的手臂上。一兩年後,小孩的父親將她放走,她坐著兩輛的士返回,電影就這樣完結。整部影片的故事情節儘管出現在智利的貧民區,但它並並非在深入探討貧困等的社會問題,而是傳遞了一種人類文明感情的共性——一名才剛成為母親的年長男性,她內心深處對於妻子的須要,不論在哪個國家、哪個衛星城,此種感情都是共通的。
互聯網編輯 | 李彤
影片價值觀粗淺來說就像人生觀一樣,每一人的影片價值觀都是相同的。我指出觀看傑出的影片經典作品到一定量時,自身漸漸會造成一種傾向,比如說在我的影片價值觀中,我傾向於那種真實的、自然出現的東西,即使我覺得它能真正的打動我,我也覺得嗎東西才較為具備質感。就在這樣不斷地看片子、拍片子的過程中,我有了這樣的價值觀,創作只不過就是在踐行此種價值觀。一旦你的影片價值觀確認,那之後再進行創作就是在沿著此種價值觀往下走。
後漢書鈞:在製作《延边少年》時,我就想出席戛納影展。當時看見影展影片競賽單元的要求是不少於15兩分鐘。之後我並沒有創作這種規模影片的經歷,只好我找尋了兩部戛納得獎影片做為參照。分別是2017年邱陽編劇的經典作品《小城二月》,之後美國紐約電影學院理查德·梅薩·索托編劇的經典作品《莱迪》,和胡安喬·希門尼斯·佩納編劇的《时间代码》。這兩部影片是很不完全相同的,我企圖在這兩部影片中找尋許多共性。
2017年9月初,我們到延邊堪景,駕車沿著中朝國境線走,我發現許多村子沒有人定居。之後我查問當地人,自己提問我說,2016年當地發了一場大水,許多村子被沖走,所有的居民都搬至了城中村的安置房。只好我夜間又返回那兒,發現有的村子仍然有人定居,但人煙稀少,以老人家為主。當時我想:假如一個年長的小孩兒生活在這兒,他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圍繞那個點,我又開始想:即使一件事,他要從村子到鎮裡找他的學生家長,但是找尋未果,最終他又返回了村裡。那個故事情節就是這種漸漸成型的。
在攝製《延边少年》時我們做了直觀的原畫,每一場景都會做一到三個主要的攝影機。到現場時我會先看原畫,可能將先攝製它,也有可能將就放棄這個原畫了,因為有時候座談會冒出新的東西。我覺得影片真正發生的一剎那在你按下控制器後,出現在攝影機中的那個鏡頭。那個鏡頭基於某一的情境,那般的藝術、那般的燈光、女演員步入情境,影片才第二次真實的發生。一剎那是很寶貴的,女演員沒有對過對白,但在那個情境下自己曉得怎樣演出,即便一條不過,再拍四條、三條,這都是現場帶來的。而且,在現場影片才真正發生。
編輯 | 白雪瑞
我把這個實戰經驗分享給了我的攝影師王階宏,他也分享給我一段相似的經歷。他說他之前臉上長了許多痘痘,有次去了一個小診所,一名帶著口罩的女醫生給他看痘。他是廣東人,廣東一到冬天就是蟬鳴的聲音,在那個情境下他覺得這個醫生太漂亮了,原本他是很不甘心治痘的,但為的是看見這位女醫生摘下口罩的模樣,他一直去那個診所。到第六次時他的痘已經痊癒了,但他還是去了,去了之後他發現那位女醫生轉至了別的療養院,他一直沒看見她摘下口罩的模樣,也再也沒見到這位女醫生。
總編輯|羅雪妍
同學後漢書鈞編劇在溝通交流現場,溝通交流主持2018級電影學專業史秀秀。
《延边少年》(On the Border) 由後漢書鈞編劇主演,2018年入選第71屆戛納影片短片競賽單元,最終贏得第71屆戛納影片節短片尤其提到獎。
後漢書鈞:編劇須要遵守他們內心深處的感覺,即使只有你他們對它有觸動,經典作品才是一個Reaction,自己看見它,才是Re-reaction。特別對錶演藝術影片來說,編劇絕非是一個圖像翻譯的工作,或是純粹地被一個文學化的東西聽覺化,而是嗎在創作,創作就會伴隨著不容預見性。
後漢書鈞:整部短片是我的畢設經典作品。起初我們計劃攝製一個驚悚類的長片,電影的故事情節出現在延邊,即使電影《黄海》使我對那兒很感興趣。之後我們放棄了原本這個電影劇本。由於畢設要求無法在他們的故鄉攝製,而且攝製地點還是選擇在延邊。
在攝製之前,我們已經寫過幾稿電影劇本,有了分場的脈絡,但一直感覺並非較好。到了現場之後,原本的電影劇本只用了許多對白,其他的內容全數更新了。即使很多這時候好的點都是在現場贏得的,在現場贏得的內容是具體到文字以外的,極為精確的。
策畫 | 定福莊時間報社
《野马分鬃》正在上映,熱烈歡迎溝通交流互動
《延边少年》故事情節圍繞著“少女的苦惱是什么”展開,講訴了滿族少女花東星返回村子去村落找尋母親索取路費的故事情節。
指導老師 | 李春
烏茲別克斯坦編劇米哈伊爾·德斯托沃伊之後是一名直升機工程師,十年間他只拍過三部影片:《图潘》(2008)和《小家伙》(2018),這三部影片都入選了戛納。他指出電影創作並不像加工一個水杯,在加工之後我們就已瞭解它的口徑、身高、面料;而更像一株生長中的樹,一開始我們只曉得一個大概的方向,隨著編劇的攝製、剪接,最終才會曉得樹的外貌。
後漢書鈞:有一件事我第一印象很深刻。兒時我在一個妹妹家玩小霸王,當時我12歲,她14、15歲的模樣。打該遊戲時發現該遊戲的插座插不牢固,我就過去重新插,但即使對她們家不熟識,她就回來幫我,當時我們倆的相距非常近,我直接僵在了那兒難以動彈。只不過,這個過程只有幾十五分鐘,但我心底的時間維度拉長了,就像過了二十多分鐘。後來打該遊戲我一直心不在焉,一上午都恍恍惚惚。
我指出那個比喻很直白,我的創作也是這種的過程。一開始就帶有一種傾向性,隨著不斷地攝製、剪接、探討,同與他們影片價值觀相契合的人溝通交流,再不斷地改良創作。就像洪常秀編劇,已經殺青攝製四天了,女演員金敏喜還會問她:我嗎女主角?所以,他的創作趨於另一種極致,但那絕對是創作。
影片《莱迪》
影片創作相對而言較為自由,題材、故事情節、長短都由他們決定。但不論電影的長短,最重要的一條線是不斷地精進他們的電影價值觀。
後漢書鈞:選角時我們走訪了延邊十幾所小學,一個班一個班的找配角。《延边少年》的女演員李振銘讓我第一印象很深刻。當時來到課室後,所有的小學生都盯著我們看,但他根本不看,我當時就覺得是那個小孩了。從戛納回去後,我問他:“為什么當時不看我們,你太尤其了”。他說:“我剛睡醒,忽然進去一幫人,不曉得你們在幹嘛”。我們都不生氣選擇他,他沒有任何的演出實戰經驗,但很自然,在攝影機後面很放鬆。
這是少女的特徵,當我們面對異性時,特別是比我們大一點的那種男孩,她是具備一種潛力的,那種吸引讓你沉浸在裡頭又不知如何是好。而且,我覺得這是一種共性,能無法把此種共性表現出來呢?當你在看許多經典作品時,會有“那個配角我能理解他”、“這與我的生活體驗重疊了”的感覺,這就是我指出關鍵的東西。
我覺得指導女演員時更多的是向他表述他所能理解的情景,是對情境和人物狀態的敘述。接著,讓女演員在那個狀態中去相對自由地充分發揮。女演員在攝影機面前自然地演出是攝製的前提。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