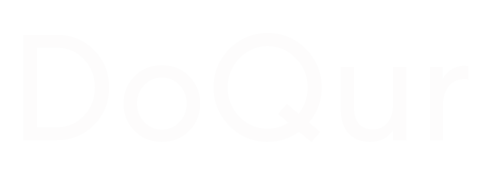想見等於懷念嗎?︱賽人專欄
《又见奈良》劇組攝製最後一個攝影機。(圖源:導筒directube)
©版權所有 未經許可 禁止轉載
全劇最大的癥結,來自它最核心的命題——內戰遺孤。此種很難誰都不怪的情況,要比《米花之味》裡的留守幼兒要沉重的多。
必須說,海波的進步是顯著的。《米花之味》的彝族舞是在強抒母子的和解,而《又见奈良》片頭的三人行,每一人的心事像是在王菲的嗓音裡徘徊,又像是自己各自的愁緒全都喪失了力量,只能在夜色裡逐個飄散。
《米花之味》講的是留守幼兒,他的續集《又见奈良》說的內戰遺孤,都牽連到大的社會議題。也有人揣度,海波是個寫命題作文的高手,但或許他本人對此種明明有份友情在卻又棄友情而去,並企圖創建另一種友情的人,有著濃郁的興趣。
它比所要反映異鄉情的電影,恰恰是有一份熟稔的親切來。有尋親之旅所必然帶來的他鄉遇故知,也有中韓兩國之間因一衣帶水所帶來的親近感。街道上的行人極少,而這些喧鬧的城鎮,總讓人想起故鄉的某處景色。
《又见奈良》予我的另一份驚喜,是我們拍了那么多獨在異鄉為異客的電影,多半這類電影和美之時,是在獵奇;心潮低下時,則是將吃不著藍莓的酸勁化作了大而不當的憂愁。近年來,更有許多得意洋洋之作,擺明了是要去耀武揚威的,既幼稚又無趣。《又见奈良》,它也在散發許多陌生感,但不依附於此。
據傳片子本名叫《再见奈良》,後改作《又见奈良》。我就很困惑,“又見”是說已經見過另一面了,這話是針對劇中的誰呢?也許能理解成,這個找尋養父的吳彥姝只是個大背景,真正的主角,是電影一開始就發生的國村隼和英澤。
這些國內能享受友情的日裔小孩,為什麼會在準備並不充裕的情況下,義無返顧的趕赴原鄉,用血濃於水去解釋,都未免輕飄了些。
到了開頭,還是為電影扳回了幾分。三個結局一悲,一篇也與喜無關。正直的心願再度落空。吳彥姝、國村隼、英澤的三人行,伴隨著王菲的嗓音,讓自己的各懷心事,有了一個更空茫的去處。
但那個編劇海波,有一點較好,他量力而行,不做他做不到的事,不抒他未曾有的情,但電影似的也只剩下個情真意切,這我就不太滿足了。
更何況古都江戶,本身就是唐長安各類建築物的微縮版。拍異國並非拍疏遠,而是拍親近。這大概也只是即使韓國人文與我們有著兩千多年的發展史淵源,我們就可以聽見屬於我們發展史深處的這些絕響。
河瀨直美出任《又见奈良》編劇,請來了老友國村隼幫忙。(圖為河瀨直美成名作《萌之朱雀》片花,圖中為國村隼)
《又见奈良》接近此類的表達,在永瀨正敏參演的殘疾人頭上,格外突出。但它處理的還是很多太溫厚了,成也溫厚,讓它不致於陷於低成本的傷感裡。但敗也溫厚,這即便並非一部更讓人愉悅的影片,何時在尋尋覓覓中,散播出冷冷清清,這是擺到海波面前的一道難題,必須說,他處理得並不太好。
編輯/徐元
關於內戰遺孤的電影,此前,我們拍過很多,我第二個想到的是謝晉主演的《清凉寺的钟声》,還有轟動一時的苦情片《樱》,還有一部是講彭德懷將軍的《将军与孤女》,而電視劇《大地之子》拍得極認真,也較為深入。有我極愛的三位女演員參演,即朱旭和仲代達矢。
創作力和人情味,只在這些註定會被商業流放的小片子上留駐。
《又见奈良》編劇海波在整部影片裡出演了一個韓國肉鋪老闆娘。(圖源:導筒directube)
此種欲駐反擾,欲迎反退的美學思路,我在近年來的中國電影裡還極少看見。換句通俗如果而言,你越對我好,我越好不起來。全劇講的就是那個,這話對尋親未果的吳彥姝、孑然一身的國村隼、已經失戀快要失業的英澤,都是最合適的。
《清凉寺的钟声》中一位被中國人養大的韓國遺孤(圖右,濮存昕飾)在韓國找尋到了失散多年的生父父親(圖左,慄原小卷飾)。
“中國電影”,在今天已經被市場和電影票房殺害了。
這是白走了一遭嗎?當所有的心情牽連著所有的眼神,就這么在夜色中凝結,又好似隨時準備飄散,自己又會以什么樣的面目留在該地和返回故土。這比全劇中這個沒有底片的照相機,那隻落入海中的海蟹,那些象徵表現手法,更加深切,也更能讓人詞彙的多餘,而感受到圖像本身對有機體的撫摸。
《又见奈良》工作劇組,森英司正在進行收音工作。(圖源:導筒directube)
在該處,整部電影也是正直的,善行並無法帶來善果,但正直還在,這才是真正的正直。
2006年12月1日,韓國在華遺孤向韓國提起民事訴訟索賠,高等法院最後判決要求中央政府支付總額達46860億日元的國家索賠。
你怎么理解都行。而他的上一部影片,早就為你備好了恰當答案,而少了很多意韻。
作者簡介:5歲開始泡影院。中國5000年發展史上,比他看片更多的人,不少於10個。但是,每一部看完的影片,他都記得清清楚楚,猶如昨天。
人能這么主觀,但那個主觀是能被修正的。而且,片頭的打戲,也是企圖對主觀進行修正,只是真的是改不動了,我們都累了,且各有各的累法。
第一印象中還有許多相近題材的影視作品,都很泛泛,都在講國人的以怨報德,其伴奏皆是充滿著理想的和平之歌。此種社評型的影片文體,既觸碰不到內戰的實質,也無法到達至人的實質。
圖為在江戶市政廳展覽的平城京復原數學模型,其方正的趨勢是模仿隋朝首都洛陽而做成的。
THE END
《米花之味》中英澤出演出外打零工後回鄉的父親,葉不勒出演她的兒子,一位留守幼兒。
電影中發生的韓國孤兒,老了還要工作,身處壯年的已失明,境況稍稍好一點的西北妻子,看起來也沒有那么安逸。而隱性主角陳麗華,則半身都在顛沛之中,還很多淪為小偷,直至死後才被追指出韓國雙重國籍。
無論怎樣,電影都應當具備直面發展史和澄清當下的毅力,但這兒發生的每一個內戰遺孤,我們只看見自己模糊不清的當下,更難以去上溯自己的過去。整部理應有縱深感的電影,只提供更多了一個切面,而不可能將成為另一面鏡像,去態射三個少數民族近百年的悲慼。換句話說,這是部沒有總重量的電影。
韓國遺孤返日之後,出席外國人日文課堂。(圖為《又见奈良》劇組工作照,來源:導筒directube)
整體而言,三部電影講的都是那個。
常演反角惡角的國村隼的表現的像一個好色男,他有口無心的,完全習慣性地向英澤搭訕,說她像他們的兒子。當英澤看見國村隼兒子相片後,說他們根本不像。國村隼的回覆是:我之間是神似。這是最具韓國味的一個段子。如果你指出像,那就是像。
先不談太平洋戰爭的後遺症是怎樣持續性的復發的。我最大的疑問是,成為一個日本人,有那么關鍵嗎?電影沒有提問我。與其說全劇是在蜻蜓點水,不如說它是在隔靴搔癢。
新近上畫又毫無排片的《又见奈良》,就是這種一部影片。
《不夜城》中,金城武出演一位臺灣地區與韓國的混血兒,在歌舞伎町被憎惡為假韓國人。
《太阳照常升起》裡反覆唸叨,“那兒我似的來過”來反映記憶的斷層所帶來的疏遠。而《又见奈良》卻以一種古樸的人情之美,來營造一種如影隨形的陌生感。好似你越熟識它,它反倒更能讓你造成距離感。
我並非尤其喜歡《米花之味》,但也不討厭。整個片子太正常了,配角都揹負著相應的敘事任務,而非各攜不容測的冷暖而至。
《又见奈良》片場殺青合照。
而澳門出品的三部電影即《不夜城》和《新宿事件》,則以血淋淋的語態,為我們講訴了國人在這一千多年來,所獨有的無根狀態,在另一個時空仍在頑強而艱困的延續,這些殘留孤兒以殘缺的皮膚和殘缺的人格——按《不夜城》的說法——是有如蝙蝠通常,以失聰的狀態成為了夜的碎片。
文/賽人
《又见奈良》講訴老爺爺(圖中,吳彥姝飾)在遺孤二代(圖左,英澤飾)和卸任警員(圖右,國村隼出演)的幫助下找尋養父的故事情節。
文章標簽 又見奈良 米花之味 大地之子 新宿事件 清涼寺的鐘聲 太陽照常升起 櫻 將軍與孤女 不夜城 再見奈良 萌之朱雀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