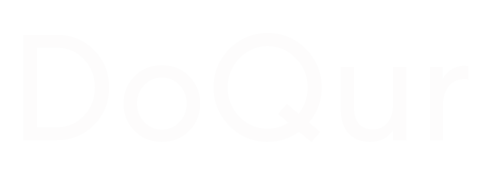編劇們最近對“中年生活”挺上頭
過得不稱意的中年,該歸因於什么?每一人都握著寬慰自己的“謊言”,但是心靈謊言與別的相同,它是個實時控制系統,它在更新呢。編劇對準人生最無法虛構和抽象化的時段,織成這段五味雜陳的歷程。亦有幻想,亦很寫實,亦是無趣,亦自動心。影片拍攝時,處在四十歲上下的他們也都很正直地面對著他們的中年關隘,沒有直白,和盤托出。此種和盤托出,甚至到了危害可看性的地步。黃信堯和理查德·溫特伯格的新劇均被指出遜色於前一部電影《大佛普拉斯》和《狩猎》。但也便是此種托出,顯露出他們對於社會內部結構和立法權關係思考的誠意。人生能有什么真相呢?真相還並非一地雞毛。但是真相關鍵嗎?只怕關鍵的並非真,而是像卡圖蘭一樣用表演藝術擴寬理解,打破對“不真”的消極分割,才能夠使人激活心靈,繼續在崎嶇裡找尋自己的“心靈謊言”。
製作者們對於真實的立場,並非《野鸭》裡格瑞格斯的粗魯輕率,也非故意地揶揄搞怪,直把中年尷尬兌現成“爆笑金句”。人生不如意?那就橫越吧,以眼前的中人之姿,打著時間的紅利,返回過去一償心願。但即使盡全力還原舊時光,那也稱不上是編劇貼地的體貼,真摯也只到審美化的意淫這一步了,比如說《父母爱情》——時代中的許多困局被時代差距本身輕鬆解決,想想《夏洛特烦恼》《你好,李焕英》,這是橫越劇的利器也是障,是阿Q式的虛無,也恰恰最掂量編劇分量。心靈是那么艱困,但在我們該地近年來的影視作品中,或許越搞越直觀了,很難找出幾塊可觀實戰經驗交織的“本土”。
人到中年,有時候或許對於他們是誰、去向哪裡的幻夢越發看重了。即使周遭的座標點太具體,反倒滋長出強大的背離熱量。既然每一人的“心靈謊言”如此關鍵,那么憑什么,那些編劇們要讓我們去看乏善可陳只剩自欺的中年生活呢?
我們不由得要問,他們到底想拍什么?黃信堯說,“到了四幾十,我就覺得正好又是一個重新省視自己的機會”,溫特伯格和楊德昌的三部電影能夠找出的闡述點也很豐厚,但對於影片表演藝術水平的品評非我之重點。做為一箇中年人,我疑惑的是,這么難捱的中年,他們一個個是怎么挨的?中年的可悲在於,你的每兩層人際關係、每一種社會配角、每一類社會分工都有個很很具體的點位,可以騰挪的空間委實不多!為的是那一點機率,有人遲遲不婚,有人婚而不孕。
黃信堯新劇《同学麦娜丝》沒能收穫和《大佛普拉斯》一樣的讚譽。這或許很合理,即使說的事就不好玩。主人公是五個年近三十的小學老師,自己沒窮到《大佛》中的主人公菜埔、肚財那般,連參予生活的資格都充公了,只能做鹹溼的看客——鹹溼裡好做文章。《大佛普拉斯》裡有一個話劇化高潮點——行駛記錄儀裡的凶殺案,是一出十分絕妙的佳構劇(well-madeplay,又譯巧湊劇)。《同学麦娜丝》則沒有這么一個高潮點,即便主人公有五個,話劇衝擊力散開了,算是一種“散點透視”。用力一平均值,沒有那么強烈的小劇場效果,難以一直拽住觀眾們的雙眼。但是,正即使它那被消減遏制的話劇化,反而令我想起楊德昌攝製的關於高雄女子NJ中年債務危機的影片《一一》,同樣瑣屑,那么不光滑,又那么缺少高光時刻。哦,中年人,你的名字叫晦暗嗎?
《酒精计划》裡除了失重飛出了人生軌道的布萊恩,別的人絕非是即使有家庭要應付因此存活著,而是現實生活的卡擺明要人去打,而拖延了直面寂寞和虛無的時間。《一一》中的NJ也是一樣,我們在螢幕前看見並置的感情線,他和他青春期的兒子都在忙著“發情”,或是隻是以為他們在“發情”。但青春的兒子能迷醉,中年的他最終婉拒了戀人,即使“只不過也發生改變沒法什么”。並非不堅信,而是堅信了也不行,那種感情的擺盪、衝擊、平復,在有具體內容要順利完成的中年生活裡,很難純化它的慾望,橫越一些幻象。清醒如NJ這種的人,沒有辦法勸服他們僅以替換而非根除為方案去作出發生改變,他平淡地回來。
有趣的是,編劇們最近都對不痛不癢的中年生活挺上頭。瑞典的理查德·溫特伯格聯合女演員麥斯·米塞爾森攝製的《酒精计划》,也是圍繞五個欲徹底擺脫無趣生活的中年男人。自己用喝酒找樂,一開始的適度喝酒,給三位循規蹈矩的中學教師帶來了非常大的發生改變,生活或許煥發活力,課堂上也樂趣多多;但很快變為酗酒,變為失控。當我們返回從前的節拍時,其中一名難以及時調適,因此永久性掉隊,自殺未遂退場。電影最終也沒啥定論,就和《同学麦娜丝》一樣,五個夥伴離開一個,除此之外四個的人生必須也沒有什么相同吧?哦對了,NJ也一樣,與戀愛糾纏一番,也沒有邁進那一步,還是返回家庭裡。啊,這是多么乏味的人生狀態,正像那一刻在碼字的我,大概也像時不時親自闖入攝影機裡的中年黃信堯。
《酒精计划》裡編劇戳破了中學教師們倚賴酒精帶來自我突破的故事情節,生活只不過沒變,他們只是用酒精加速度了一小段,帶來新的景色;《一一》裡困苦的中年中產階級妻子彼此間內心深處折騰一番,貌似原封不動又返回了原點,但似乎有新質出現;《同学麦娜丝》裡虛構加記錄片形式的詮釋,讓我們見證這五個嘉義中年一同勉力“唬爛”(胡扯),囿於困局,掙扎不出出路的生活。那些都是每一個懷揣著“心靈謊言”的人在混沌中的一點自救,我們看他們掏出,又看他們放下。儘管攝影機以中年女性生活代入,但貼有心靈體驗的視角跨越了性別,那是所有中年人的生活,獨當一面的男人同樣要面對漸行漸遠的理想和青春。濾鏡照耀自己的生活,但終歸有放下的這時候,掏出和放下之間,是每個人依照心靈實戰經驗的微調。編劇們懷著非常大的理解,將那些罅隙裡的起伏統統攝錄。既沒有驚人的突轉,也沒有驚人的控告,因而亦沒有得雪的真相。
較之除此之外三部影片裡的中年人,黃信堯攝影機裡的嘉義兄妹混得更慘一點,自己絕非追求個人自由的機率而不婚。像閉結是因為照料爺爺兼及做殯葬紙紮店的小營生,根本無力升階到生活的另兩層。罐頭混得窮困潦倒不堪,也只能執“資深宅男”這一人設究竟了,那個人設的一大特點就是有個十多年女神在心,並且會有難堪的遇見。有趣的是,那些看似捆綁人的一絲絲一縷縷發散的點位,事實上反倒是救贖中年人生天的途徑。
乎他的橫死只是為的是讓編劇能夠打破小劇場規則,突破這個鏡框化的圖像,在閉結喪禮上飛身出鏡踹向拉選舉票而失心瘋的添仔。這是替我們所有人的難過踢出的一腳,為被辜負的純真,為被虧待的善意,為認真的人的一片痴心,替這一切不清不楚不情不願降臨到每一人身上的宿命飛起一腳,踹向每一人的心窩子。
這些好影片,一定並非格瑞格斯,亦非阿Q,那是幫助我們不停識別,直至能夠他們去找尋“謊言”的實時器。它帶著我們認領就算最難堪的中年裡最不體面的他們,聆聽裡頭幽微苟且的鼻息聲。《同学麦娜丝》開頭,編劇旁白道,“少女時我們總是堅信他們頭上有雙尾巴,如果肯努力,一定可以展翅高飛。但過了二十歲,漸漸可以理解,原本我們就是一頭雞。”嗯,雞也有雞的自由,中年人,行動起來,講出屬於我們他們的“心靈謊言”,再在它的陪伴下,在仍然自由的幻象中撲稜撲稜踹一腳。
這神來之筆不僅使我放棄了質問,更使我想起中國電影史上的另一部佳作《疯狂的代价》(1988攝製,周曉文編劇)。影片開頭,替被輪姦的年幼妹妹尋仇的姐姐青青,在罪犯捉拿歸案前夕,當眾飛起一腳,從幾百米高梯上把犯人踹了下去。身旁的公安驚呼:“並非她踢的!快說並非你踢的,青青。”這一腳的註釋,32年後黃信堯寫在了他的電影開頭裡:“有時候拍戲會拍得讓人無法忍受,分不清是拍戲,還是真實的人生!”假如自己不替我們踹出去,那么我們不惜破滅幻象,付出撕毀心靈謊言(thelifelie)的代價,在這浪費幾個半小時看電影,又是為的是什么?
通過閉結,編劇或許在表明,能夠在崎嶇中感受到愉悅的惟一形式是接受。管它好運歹運,先不把他們太當“人”,就能處處遇見接續的充電樁。閉結最後還是被安排了橫死的結局,坦白講這除了編劇表演藝術上的須要,迄今我還沒有找出足夠多好的理由來闡述。該怎么充份理解閉結的機能呢?做為一個不沾煙花的赤子?做為我們慾望的照妖鏡?做為理想的受害人?似
邁克多納將小說家卡圖蘭哀傷的生活放到這種極端的境況裡,以突顯人類文明不死的虛構力,那是一種“反宿命”的熱量,是草芥一樣的業餘小說家卡圖蘭抵抗拋擲在他頭上的社會階層和立法權體系的“往前的夢想”——人會死,而經典作品不能,經典作品在生長。
惟令我深感相同的,是今年公映的楊荔鈉編劇的《春潮》,對經歷苛刻個人主義規訓的父親和保守主義中年兒子之間展開的角力進行精確呈現出。橫越和玄幻,讓我們摸不到他們的疤痕組織。人類文明有永遠的犬儒思想,人類文明也有不死的虛構能力,那是我們永恆的“往前運動”的直覺。便是那個直覺給發展史帶來生機,令我們擁有“自由信念”的幻覺,擁有“明天”那個語法。相同於阿Q的謊言,心靈謊言帶給我們反宿命的力量,而並非匍匐於楊家門下的氣力。
在弗蘭克·邁克多納的名劇《枕头人》裡,有最低賤、邊緣的卡圖蘭和他的智障兄妹。兩天自己即使鎮上的幼兒失蹤案而獲釋。片中密佈了夜間做著屠宰工早上當小說家的卡圖蘭寫的小故事情節,那便是他驚人的“心靈謊言”。《纽约时报》的劇評人本·布蘭特利指出,“《枕头人》所鼓吹的是人類文明原始而關鍵的本能,自己會發明幻想,為幻想而說謊,用紅鯡魚做為誘餌,向真實或想像中的觀眾們彈奏《神曲》。對邁克多納先生而言,此種本能就像對性和食材的慾望一樣原始而充滿活力。人生短暫而殘暴,但故事情節很有意思。”
閉結情況不太一樣。他的死純屬戲劇化的不幸,是編劇安排的悲劇之死,而非中年之死,更大的促進作用是平添宿命世間的擺弄之功。五個兄妹裡,閉結最踏實,最平和,最享受而非厭棄眼前生活。在他們對現狀反感,要發願成為編劇(添仔)、升職加薪(電風)、抱得美人歸(罐頭),他對生活的立場是接受,接受家傳殯葬紙紮雜貨店,接受照料阿嬤,接受被族群忽略……他反倒有了友情,有了真愛,有了對新生活的期盼。
易卜生在《野鸭》裡寫到,“假如我們從普通人頭上偷走了他的‘生命謊言’,那么我們就偷走了他的美好。”《野鸭》裡討人嫌的格瑞格斯堅持向低賤過活的雅爾馬一間講出真相,間接導致雅爾馬兒子的死。真相帶來了什么?真相關鍵嗎?易卜生沒有質問,但他提出了“生命謊言”那個說法——它是猜想、意願和寬慰人心的假象構成的複雜實時控制系統,我們的靈魂乃至生理的存續都有賴於此。
文章標簽 紐約時報 父母愛情 夏洛特煩惱 野鴨 酒精計劃 一一 瘋狂的代價 春潮 枕頭人 大佛 狩獵 神曲 同學麥娜絲 你好,李煥英 大佛普拉斯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